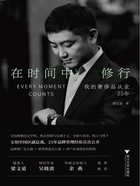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2000年年底的一天,我接到卢克勤(Kevin Rollenhagen)先生打来的电话,他问我是否愿意接手一个进入中国内地市场不久的高级腕表品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宝珀”这个名字。
卢克勤来自美国,是钟表行业大名鼎鼎的教父级人物。他于1989年加入斯沃琪集团,彼时担任欧米茄(OMEGA)和宝珀在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的副总裁(澳门市场亦归其管理),并负责斯沃琪集团旗下多个奢侈品牌的管理工作。
此前我对手表并无研究,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做人要艰苦朴素,避免铺张浪费。上高中时,父亲给了我一只电子表;工作之后,我曾收到过一只浪琴(Longines)手表作为生日礼物——那是我拥有的第一件奢侈品。
大学毕业后,我所从事的工作与奢侈品毫无关联。我先是在酒店行业工作了将近三年,之后加入一家韩国食品企业,从首席代表助理一路做到销售经理。在食品快消行业摔打了五六年后,我下决心要离开。坦白说,我对奢侈品的了解是从入行后开始的,相较于那些从小就有机会出国见世面,年纪轻轻就对时尚行业如数家珍的富二代,我对奢侈品的认知起步不算早。但俗话说,“好饭不怕晚”,入行的那个时代给了我从0到1的好机会。
宝珀诞生于1735年,是第一个在瑞士注册的钟表品牌。自品牌创立,宝珀坚持只做机械表,每一只顶复杂的机械腕表都以手工制作。宝珀也是世界上极少数可以自主完成设计、研发、制造、组装、销售等全流程的钟表品牌。1992年,由尼古拉斯·海耶克执掌的斯沃琪集团的前身——瑞士微电子技术及钟表联合公司(SMH),从雅克·皮盖(Jacques Piguet)与让-克劳德·比弗(Jean-Claude Biver)手中收购了宝珀和FP机芯工厂,使得斯沃琪集团除了拥有低端、中高端手表品牌,也在高级奢华腕表品牌的行列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宝珀是一个承载着瑞士悠久制表历史的品牌,有着深厚的制表工艺的底蕴。在20世纪90年代,宝珀的顾客群体涵盖了当时全球最富有的人物,如文莱苏丹的皇室贵族,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钟表爱好者。宝珀现任首席执行官海耶克先生于2002年全面接管宝珀,成为宝珀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在他的领导下,宝珀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2001年,宝珀计划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并招聘专门人员来负责拓展其在中国内地的业务。当时,内地白领阶层中的中层管理人员,月平均收入在1万元,而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奢侈品”腕表是同属斯沃琪集团、均价在1万元以内的雷达(RADO)。对于宝珀这样一个平均单价超过10万元的高端手表品牌来说,想要在内地市场打开局面,其艰难程度是显而易见的。


瑞士汝拉山谷的维莱尔(Villeret)小镇,近三个世纪以前,宝珀就诞生在这里。照片摄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宝珀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一批忠实用户。
今天的宝珀大复杂制表工坊。制作一款复杂的机械腕表需要五到六周甚至更长的时间。从组装机芯开始,一步步为腕表加入从简单到复杂的各项功能,并进行细心调校。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但制表师却甘之如饴:“在宝珀我们很幸运,可以从最开始的主夹板做起,完整见证一件腕表作品的诞生。”
我请卢克勤先生给我一些时间来考虑,我需要对宝珀这个品牌以及这份工作进行必要的前期了解和市场调研。我打听到,北京的东方广场名表城有宝珀的柜台,我假扮成对高端腕表感兴趣的顾客,主动与营业员攀谈,了解品牌的基本信息和销售情况。我了解到,作为斯沃琪集团旗下的高级奢华腕表品牌,宝珀在内地知名度不高,常常一个月也难以卖出一只表。当然,彼时相同价位的高级腕表的销售情况基本上差不多。
我的推荐人——已在斯沃琪集团工作两年的好朋友汪久峰(因为英文名叫Jeff,所以大家都叫他“姐夫”)也为我提供了一些品牌的市场数据和内部评价,这些数据和评价皆证实了宝珀在中国内地尚在起步阶段,受知名度和影响力所限,销售乏力。我原本担心这些信息会打消我的工作积极性,没想到反而激发了我的好胜心——既然宝珀目前在内地市场的发展不如预期,岂不正说明我有很大的机会和空间做出一些成绩?
我欣然接受了卢克勤先生的offer,于三个月后正式入职,成为宝珀在中国内地的第一名员工。
我所加入的宝珀隶属于斯沃琪集团,斯沃琪集团创始人尼古拉斯·海耶克是瑞士钟表业的传奇人物,被尊称为“斯沃琪之父”。面对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石英技术对钟表行业的冲击,尼古拉斯·海耶克带领瑞士钟表品牌走出了危机,重振了瑞士钟表制造业,被视为瑞士的民族英雄。他创建的斯沃琪集团是世界上知名的钟表集团,曾占据全球中高端钟表市场65%的份额。斯沃琪集团拥有包括斯沃琪、浪琴、欧米茄、宝珀、宝玑、海瑞温斯顿在内的17个腕表珠宝品牌。斯沃琪集团在瑞士地位崇高,曾被评为“瑞士受欢迎的企业”第二名——而第一名,是一家救援公司。

我的恩师卢克勤
2001年5月,我时隔20年再次回到上海。这里和我童年记忆中的样子变化不大,街巷交错、市井洋腔,繁华中透露着冷淡和疏离。一个人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在这座城市里留不下一点痕迹。
我在舅舅家暂住了一段时间,一找到合适的房子便主动搬了出来。我在徐家汇附近租了间一居室,这间一居室面积不足20平方米,墙上糊着报纸,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房间里仅有一张双人床、一个储物柜和一套简易桌椅——既能用来吃饭,也可用来临时办公。我不经常待在家里,狭小的室内空间让我感到逼仄和压抑,我更愿意一个人出去走走,哪怕只是在附近的商场漫无目的地闲逛,也可以是对零售业的观摩和学习。
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那几年对我来说一直萦绕不去的情绪叫作“孤独感”。从小被教育“男子汉要顶天立地”的我不想去正视这种感受,我一度认为这种感受是软弱和无能的表现,在一个30岁的男性身上出现是不适宜的。
我的办公地点在徐家汇美罗大厦——一栋26层高的综合性写字楼。在同一栋楼里办公的还有百胜、微软等跨国公司。当时,作为宝珀在中国内地的唯一员工,我没有一个专属的办公空间。而同一办公室里负责斯沃琪集团其他品牌的同事大多为上海本地人,他们在日常交流中习惯使用上海话。我明白他们并非有意排外,但对于长期居住在北京的我来说,这种语言环境确实让我感到有些格格不入。虽然我能听得懂上海话,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我仍然感到难以完全融入。
我从小在上海跟着外婆一家长大,听懂上海话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我那几年坚持用普通话跟人沟通。在潜意识里,我拒绝被上海这座城市同化。我甚至天真地以为,这段在上海的工作经历只是我职业生涯中的过渡,我从来不属于这里,早晚还是要回到北京的。
我在上海没什么朋友,下班之后无事可做,也无处可去,办公室便成了我最常待的地方。很难说是工作让我选择了孤独,还是孤独迫使我选择了工作——从结果上来看,这二者并无分别。工作让我感觉充实而踏实,让一个蹉跎数年的年轻人重新找到了方向。只有在工作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而不是一个三十几岁背井离乡、独自一人在沪上闯荡、身无长物且居无定所、前途未卜同时后路未知的男青年。
后来,我因工作关系接触过不少毕业不久,对前途尚且迷茫的年轻人,他们同我当年一样:满怀一腔热血,却苦于无处施展拳脚;空有一身抱负,却找不到确切的前进方向。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那是每一代年轻人都会经历的、需要靠自己一个人挨过的“至暗时刻”。没有人陪你一起上路,没有人告诉你这条路会有多长,没有人知道前方的黑暗还要持续多久。只有迷雾被冲破的时刻,才是真正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