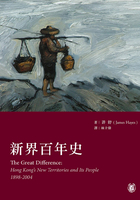
新九龍
走筆至此,是時候談一談新九龍了。這面積七平方英里半的土地,位於1860年割讓給英國的舊九龍北界圍欄以北。(66)這片土地有九龍山脈作為屏障,與新界其他地區分隔,英國人馬上認為它「重要性愈來愈大,是本殖民地擴展之處」,而且「表面價值遠比新界其他地區為高」。(67)此外,如駱克在1899年所說,由於此地與舊九龍和香港島接近:
所以相較於較偏遠地區的鄉民,這裏的居民較願意接受西方的方法,也較能理解他們所要遵守的規矩的意義。(68)
因此,新九龍被劃入此殖民地原有的市區,而管治香港其他居民的法規,新九龍居民也須一概遵守。(69)
在1906年「對本殖民地這一地區首次進行的詳細人口普查」中,新九龍被描述為「由深水埗和九龍城兩個警區組成」,人口有15,319人;(70)更為詳盡的1911年香港人口普查,則列出了大多數(但不是全部)古老的大小村落。(71)從一些跡象可見,政府對待此地區的這些舊居民,態度並非那麼慈父式,那些遺漏是其中之一。(72)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如此。在九十九年租借期內,相較於九龍山脈以北的村民,新九龍村民的遭遇非常不同,所得的照顧也少很多。這兩批人迥然相異的命運,會在第八章論述。
(1) Royal Princes, Vol. II, pp. 208-209.
(2) 譯註:即伊莎貝拉·伯德(Isabella Bird)。
(3) 她對於此地的歐籍人就不那麼有熱情。
(4) Curzon, p. 428.這迥異於1840年代的輿論,1840年代的某些作者認為應該取舟山而捨香港,因為香港是個「不利於健康、瘟疫肆虐,而且無利可圖的荒島」,「是由原材料構成,而且不曾被文明觸及……的殖民地」:如見Sirr, Vol. 1, pp. ix and 179。
(5) Gordon-Cumming, Vol. I, p. 5.
(6) Vincent, pp. 305-310.
(7) Hübner, p. 576.譯註:文特諾和尚克林是英國懷特島上兩個海邊渡假小鎮。
(8) 在芸芸關於老香港及其居民的攝影集中,以弗蘭克.菲施貝克(Frank Fischbeck)的FormAsia公司出版的攝影集和Asia Society Galleries的Picturing Hong Kong最有名。FormAsia出版的Building Hong Kong考察了全香港包括新界的建築。
(9) Des Voeux, p. 37.政府在1885年成立了一個土地委員會,調查維多利亞城人口過於稠密的問題,該委員會建議以填海來舒緩擁擠情況:Abstract, pp. 28-29。工務司就此問題提交的報告,見SP 1887, p. 318。
(10) 譯註:後來稱為立法局。
(11) Hansard 1897-98, p. 5.
(12) 這句話出自1902年6月定例局通過水務條例草案的時候。見Hansard, 1901-02, p. 28。
(13) 「平民人口主要是成年男性,在華人人口中,男性……至少佔百分之七十二點九。」Report of the Sanitary Board for 1901 in HKGG, 2 May 1902, GN 265, p. 721.
(14) 許布納清楚指出,來到香港的華人,比起他們留在中國國內,可以接觸到更廣泛的各色人等。「在城內的低下階層區域,風景都富生氣和繁忙:穿紅色制服、膚色黝黑的官兵(印度兵)、帕西人、印度人、華人、馬來人、穿著優雅的歐籍女士,以及膚色淡黃、衣飾如歐洲人的男女(混血的葡萄牙人)。」Hübner, p. 576.他還說:「沒有人想步行。除了轎子,見不到其他事物。」〔這是11月底,全年天氣最好的季節!〕另一名來訪者密福特(A. B. Mitford,後來獲冊封為里茲代爾勳爵[Lord Redesdale])在1865年前往英國駐北京公使館履任時途經香港,他生動地觀察到這些「各色人群猶如沙律中的油和醋,無法調和融合」:Mitford, p. 5。
(15) 入籍英國須由定例局以通過法例的方式予以批准,如見HKGG, 14 January 1888及Hansard 1902, p.18。新界割讓給英國後,新界居民亦可入籍英國。見圖十七。
(16) 這裏不談英治初期的九龍,見Hayes 1983的相關章節。
(17) King, p. 70.他的這段描述發表於1911年,但管理水上人的法規,早見於十九世紀。這些船舶在夜間停泊在一起的原因,是因為政府禁止船舶在晚上在港內航行。關於1841和1862年的《港口條例》,見Wells Williams, pp. 217-220。
(18) 見Arlington in Hayes 1983, pp. 29-30。
(19) 關於採用英國法律的決定,見Munn, pp. 163-169。然而,在法庭以外,東華醫院肩負起仲裁華人糾紛的責任,與法庭形成競爭(有些外籍人知悉此事並加以譴責,見Munn, p. 377),而同業公會、華人行會和社團一定也做同樣的工作。古老的鄉村實際上也依循風俗習慣,尤其是關於土地和房屋擁有權方面的事情,如果華民政務司保存的鄉村地租登記冊沒記載業主姓名,只要家族中有人每年繳付地租,土地就可以一路繼承而無人去質疑。有關香港古老村落的資料,見Hong Kong Land Commission 1886-87, Report in SP 1887。
(20) 譯註:後來稱為行政局。
(21) 也稱為「撫華道」,他的部門名稱在1913年改為Secretariat for Chinese Affairs(譯註,英文名稱原為Registrar-General's Office,但中文名稱在早期的《憲報》中已經譯作華民政務司署)。每年出版的《藍皮書》(Blue Books)詳列文職人員編制,財政狀況則見每年出版的《殖民地開支預算》(Colonial Estimates)。當年駱克身兼華民政務司和輔政司,關於當時華民政務司手下的全體人員,如見BB 1901, pp. I 50-53。
(22) 為適應本地情況而有所修改。另見Bickley 2005。
(23) Hansard 1900-1901, pp. 29 and 32-33.何啟博士說,掃石灰水已證明並非防疫良法,並且對於住在鄉村的「窮人來說,既不必要又擾民」。不准在山頭下葬,以及不准在官地上的政府植林區割草砍柴的禁令,對香港島和舊英屬九龍的村民來說,是影響很大的措施,如參見言詞嚴厲的警察告示:Police Notification in HKGG, 1 April 1876, and Hayes 1983, p. 65。
(24) Albert Smith, p. 39. 1859年政府公告第十二號說:「較大型的學校也教授基本的英文拼寫和閱讀。」(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for Superintending Government Schools for the year 1858”, printed in the HKGG, 12 February 1859 as GN No. 12)在1858年有十五所學校,學生則有六百七十五人。所有鄉村學校都受政府的教育計劃管轄。
(25) 譯註:後世把他的名字譯為「史釗域」,但在當時的《香港轅門報》中,他所用的漢名是「史安」。
(26) 譯註:當時該校英文名稱為Central School,中文稱為國家大書院,掌院即校長。
(27) Bickley 1997, pp. 88-91 and 103-113.
(28) 見Carl T. Smith 1984 and 1995。
(29) CSO Ext 1903/9284是談在坪洲徵收地稅問題(Gompertz to Hon. CS, minute of 8.12.03),「據我所知,島上有九十或一百間住宅,而當地長老把兒子送到皇仁書院念書。」
(30) 施其樂(Carl T. Smith)牧師口頭證實此事。衙門是中國官員的官署和官邸。
(31) SP 1897, The Educational Report for 1896, para. 9.另見Ng Lun 1984, pp. 139-146。
(32) Education Report for 1896, para. 7.
(33) 1912年成立香港大學(Endacott, p. 283)是向前邁進的另一步,情況就如1907年創辦香港實業專科學堂一樣,這所學校是教授多種實用科目的夜校:Endacott, p. 281, and BB 1911, p.12。
(34) Beresford, pp. 466-468.
(35) Beresford, “Summary of Trade Statistics” at pp. 480-481. Remer, p. 100說:「在中國對外貿易史上,英國航運在十九世紀末葉的重要性是前所未有的。」但比利時駐華總領事兼代辦尤勒斯·迪克斯(Jules Duckerts)卻認為這個港口被高估。Duckerts, pp. 115-116。
(36) Beresford, pp. 216-233.他們同時指出,雖然他們從這個殖民地取得英籍身份,但英國駐華領事沒有保護或協助他們,使他們甚感失望懊惱。
(37) 貝思福訪華時所見過的人,包括一些思想進步的中國總督,他們公然為國家感到憂慮,並且宣之於口。該書指出歐洲列強急欲劃分「勢力範圍」和其他租界,藉此瓜分中國。這種情況加強了香港和其他在華英國飛地的地位,並令這些地方的英國和其他西方居民更加不可一世。另見本書第十一章第289-290頁和293-295頁。
(38) LR, p. 552.
(39) 在1910年,史都活(Murray Stewart)議員在定例局憶述英國接收新界時的落後狀態,他說:「那裏可見修築了圍牆和壕溝的村落,完全沒有道路,因此沒有車輛交通;商業就是小販的販賣活動……因此限制了買賣商品的墟市地區,你會覺得那裏的農耕方式很原始,居民又落後保守。想要促進文明,主要方法就是靠交通運輸。」Hansard, 1910, p. 113.他還說到「新界鄉民和本殖民地居民之間的差異」仍然存在。Ibid., p. 114.韓美頓(Eric Hamilton)在1958年寫給我的信,也強調關於當時新界的這種情況(「香港島南岸其實也是如此」)。Hamilton Letters, 1 August 1958。
(40) 在香港島和舊英屬九龍,恰巧都有類似駱克在新界所見的古老鄉村。這些聚落位於擁擠的市區之外,繼續傳統農耕,那裏的生活大概與內陸大同小異。但這些村落數目不多,居民加起來只有幾千人,對這個殖民地的管治方式毫無影響力,而且許多男村民都到海外謀生或當海員。
(41) 摘自駱克呈交卜力的機密備忘錄,這份沒寫日期的備忘錄,附於他的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史奧娜·艾爾利也有引用(Airlie, p. 103)。另見SP 1899, p. 179, para. 12。
(42) 地保是由官府委任的半官方人員,負責鄉村保安事宜。見Ch'u, pp. 3-4 and Watt, pp. 190-191。
(43) 如我們所見,在中國,縣以下的分區有多種叫法,「洞」是其中之一。
(44) CO 129 284/242.香港這個殖民地沒有地方行政的傳統。雖然土地委員會在1886年曾有此建議,但警署仍然是獲得地方知識和聯繫偏遠地區居民的中心。如見Hayes 1983, p. 53。
(45) Clyde, p. 840.
(46) 見Hsiao, pp. 373-374。
(47) 英國駐華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在1849年寫道,在暴亂或騷動的時候,「中國人知道,如果他們被盯上或認出,他們和家人在亂局結束後,可能遭到可怕的報復,這個想法令每個中國人為之膽喪」:in McNair, p. 216。
(48) 在十九世紀末,兩名重要總督(譯註: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上奏朝廷,他們在建議中說:「差役之為民害,各省皆同,必鄉里無賴,始充此業。」(No. 226 in Hirth)關於低級官吏貪贓枉法的事例,如見Hayes 2001.1, pp. 13, 17, 24 n3。
(49) 翟理斯(Herbert Giles)觀察了許多中國官員和他們的行事方式後,形容中國政府的形式「本質上是專橫殘暴」:Giles 1882, p. 122。遭遇船難的顛林(Frank Denham)船長心懷憤恨地記載在1840-1842年鴉片戰爭期間,自己與船員落入地方官員手上的遭遇,他說,他們必須絕對地服從的,「並非法律規定,而是他們〔中國官員〕任意發出的命令」:Denham, p. 3。
(50) 康熙皇帝就親口說過這樣的話:van der Sprenkel, pp. 76-77(譯註:原文為:「若庶民不畏官府衙門且信公道易伸,則訟事必劇增。若訟者得利,爭端必倍加。屆時,即以民之半數為官為吏,也無以斷餘半之訟案也。故朕意以為對好訟者宜嚴,務期庶民視法為畏途,見官則不寒自慄。」)。另見威妥瑪(T. F. Wade)的譯文:Wade, Vol. 1, especially No. 74 on pp. 63-70。
(51) 如見伊莎貝拉·伯德(畢曉普夫人)對於中國司法和監獄駭人聽聞的描述(part of Letter IV between pp. 67-85, during a visit to Canton in 1879);較早期的情況,另見Wingrove Cooke, chapter XXIX。
(52) 翟理斯斷言,中國民眾「認為,泰西所不能忍之事,他們大都加以容忍,是正確之事」。他說:「中國人自認為是須要受管治的民族。」但他也把這種情況歸因於一點,就是人人皆可參加科舉考試,而大部分官職都是從科舉選拔的人才充任,因此,(如他所貼切地說)他們「同意把脫穎而出的考生視為主子,而非公僕」。翟理斯也看到統治者的強大權威,有部分受到「百姓實際的民主精神」所抵消,而且他們還獲支持去對抗「在高位者明目張膽的惡行」:Giles 1882, p. 122,他還舉了幾個民眾對付苛刻或不受歡迎官員的事例,見該書第224-225頁。另見Hayes, JHKBRAS 30 (1990) pp. 6-11。
(53) 見本書第三章,註45。
(54) Peplow, pp.140-141.在1950年代初,高志(Austin Coates)注意到另一個特點,他斷言「八成來理民府的人,說起話來都像在打啞謎。員工多年來經驗豐富,已是司空見慣。」他認為這是「由於他們心智能力有所不足,無法有條理地敘事」:見其小說《大路》(The Road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9]), pp. 298-9。在其經典著作《洋大人》(Myself a Mandarin,1968)中,他把這個主題再加以擴大。
(55) 據伊莎貝拉·伯德記載,廣州囚犯很清楚香港監獄犯人得到較佳待遇(Bird, p. 71)。
(56) 它們包括九龍城、位於新界的現有中國稅關、北部邊界的劃分,以及深圳谷應否納入九龍展拓範圍。這些不同的問題可以參見CO Hong Kong Correspondence和Extension。1899年3月11日達成劃定新邊界的協議,3月19日簽署《香港英新租界合同》:Wesley-Smith 1980, pp. 198-199。
(57) 至今有關這場戰鬥和整個事件最精采和鉅細無遺的論述,是夏思義的新文章“The Six Day War of 1899”,此文將在JHKBRAS發表(譯註:已出版成書The Six-Day War of 1899:Hong Kong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並有中譯本)。另見Groves 1969。
(58) 根據官方報告的估計,中國人方面的死傷不大,但夏思義仔細分析過地方上保存的資料,認為反抗軍傷亡很慘重,我認為他所舉的證據十分確鑿。圖八所見的大型義塚與那次抗英戰鬥有關,該義塚位於錦田附近的沙埔。對於英國租借新界時期官民關係中的這樁不幸事件,人們似乎很想忘掉,因此,葬在該墓或其他地方的戰死者(包括男女),沒有像在村落械鬥中陣亡的英雄那樣,在春秋二祭受人追念。結果,這個墓塚被後世村民和歷史學家忽略,但港府在1994年修訂《新界條例》,賦予女性繼承土地的權利之後,村民重新發現並修繕這座墓塚,鄉議局在其保鄉衛族的政治運動中加以利用。見Selina Ching Chan 1998,以及本書第十二章第332-334頁。
(59) 有些繪影繪聲的傳言,說英國人很可能待民殘暴、干涉居民生活,並且徵用土地,令抗英運動火上加油,見Wesley-Smith, pp. 83-85, and Groves, pp. 43-45。在報紙出現前的時代,一般民眾容易聽信謠言而恐慌,如見以下很有啟發性的記載:Moule, chapter V, Griffith John in Wardlaw Thompson, pp. 394-396, and Stott, pp. 45-51。後來香港出現的例子,見SP 1921, p. 156。
(60) Extension, pp. 21, 26, 28.然而,卜力後來把《1889年收回官地條例》應用至新界,並將其涵蓋範圍擴大至「任何種類的〔公共〕用途」,為日後大規模收地鋪路,這似乎牴觸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關於徵收民地的條文:HKGG, 7 October 1899, and Hayes 1993, pp. 66-67。
(61) 「若無法提供土地業權文件,在向該鄉村和地區發出適當通知後,正在佔用該土地的事實,也會獲接納為擁有權的證明。」港督在1899年4月12日向駱克傳達「關於九龍展拓地區現有行政」的指示:Ibid., p. 41。
(62) No. 186 of 13 May 1899 to London, in CO Hong Kong Correspondence. Also Airlie, pp. 101-102.夏思義在其新文章“The Six Day War of 1899”中,詳細探討兩人對於平定反抗所持的迥異態度。
(63) First Year, pp. 12-14.這些委員得到茶、蛋糕和雪茄招待,他們的回覆載於CO HK Corr., No.243。在另一例子中也可見到卜力這種率直的性情,那就是他在1903年親自到維多利亞城疫區,解釋他如何應付疫症:Boyden and others, p. 70。
(64) 一開始時並不受人歡迎。「新界居民很厭惡和反對設立警署,他們對於選址工作百般阻撓,阻撓不果後,又不協助建造工作」:SP 1900, p. 241。這種對抗心態,肯定是因為在中國統治下,縣衙差役普遍聲名狼藉。見本章註48。
(65) 更詳細的描述,見第四章最初幾頁。
(66) 今天的「界限街」就是由此而來。關於這道邊界圍欄,見Decennial Reports。圍欄的照片見Peter Wesley-Smith 1980, at Plate 11,以及p. 30 of the Urban Council's Hong Kong Album (1982)。
(67) 多年前抄錄的資料,出處已無從稽考。另見駱克的意見(First Year, p. 1)。
(68) 類似的說法見HKGG 1900, GN 201, p. ii。
(69) 根據1900年第八號《法律延伸條例》(Extension of Laws Ordinance)。「為了提供適當行政,並促進此地區發展,必須把港九市區實行之衛生、差餉和其他法律應用於此地」:見修訂1911年《釋義條例》(Interpretation Ordinance)的法案第一款「目的及理由」。政府還繪製了一個此地區的修訂圖則。見HKGG 1937, p. 879。
(70) SP 1907, pp. 258, 276.
(71) SP 1911, Table XIX (a) at p. 103 (39).
(72) 蒲崗、衙前圍和竹園這幾條重要的古村,以及許多位於新九龍中部、較後期建立的村落,全被籠統地歸入「九龍城」,而沒有列出其名字,儘管有此瑕疵,但這是關於新界大小村落最詳盡的列表。新九龍沒有像新界那樣委任分約鄉事委員(見GNs 387 and 394 in HKGG for 8 and 15 July 1899),因此史家無法知道關於新九龍各分約、村落和領袖(分約鄉事委員)的資料,妨礙了我們對此地區在1898年前狀況的了解。這也顯示出政府對於新九龍鄉村的不同態度。柯美(G. N. Orme)也提供了另一個例子,他說,新九龍的官契承租人並未獲得土地憑證,「因為他們通常對自己的土地暸如指掌,而且對他們來說,去香港查閱登記冊也是輕而易舉」(Orme, para.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