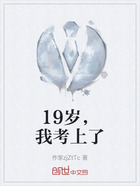
第8章
九月初的长沙,暑热未消。陈晓阳拖着疲惫的步伐走进教育学院大楼,手里攥着一份休学申请表。他已经连续三周没去上课,期中考试全部缺席,辅导员下了最后通牒。
拐角处,一个熟悉的身影让他猛地停住脚步——周教授正抱着一摞书从办公室出来。
“陈晓阳?“周教授推了推眼镜,“正好找你。进来谈谈。“
陈晓阳张了张嘴想推辞,但周教授已经转身回了办公室。他只好硬着头皮跟进去,悄悄把休学申请表塞进背包。
周教授的办公室堆满了书籍和文件,唯一整洁的是墙上挂着的一幅黑白照片——年轻的周教授站在一所简陋的乡村学校前,身边围着一群孩子。
“坐。“周教授指了指椅子,自己则靠在桌边,“听说你这学期遇到了些困难。“
陈晓阳低着头,不知从何说起。汗水顺着他的后背滑下,浸湿了廉价T恤。
“我...家里有些事。“他最终挤出一句。
周教授摘下眼镜擦了擦:“苏晴告诉我了。“
陈晓阳猛地抬头,胸口一阵刺痛。他没想到苏晴会跟周教授谈起他的家事。
“别误会,她很担心你。“周教授仿佛看透了他的想法,“我也是。你是我这几年见过最有潜力的学生之一。“
“我现在没资格谈什么潜力。“陈晓阳苦笑,“连学费都交不起。“
周教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知道我为什么研究乡村教育吗?“
陈晓阳摇摇头。
“我出生在贵州一个比青岩还穷的山村。“周教授的声音平静,“父亲早逝,母亲靠编竹筐供我上学。高二那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我决定辍学去广东打工。“
陈晓阳惊讶地看着周教授,难以想象这位风度翩翩的学者有这样的过去。
“是我的高中班主任连夜走了二十里山路来我家,说服我母亲让我继续读书,还垫付了学费。“周教授的目光投向窗外的远方,“那笔钱对当时的他来说不是小数目,但他坚持不收借条,只说'以后有机会,帮助下一个孩子'。“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时钟的滴答声。
“后来呢?“陈晓阳忍不住问。
“后来我考上了师范大学,留校任教,一直想找机会报答那位老师。“周教授笑了笑,“可当我终于有能力回报时,他已经去世了。所以我选择帮助更多像我当年一样的孩子——这就是教育的传承。“
陈晓阳的喉咙发紧,他想起了刘强,想起了自己曾经得到过的帮助。
“接受帮助不是耻辱,陈晓阳。“周教授的声音变得柔和,“真正的强者不是永远不依靠别人,而是懂得在需要时接受帮助,然后将其转化为帮助他人的力量。“
一滴汗水从陈晓阳的额头滑落,砸在他的手背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把自尊与固执混为一谈。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头。“他艰难地开口,“已经错过了太多课,还有那些被我推开的人...“
周教授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教育部的一个特别助学金申请,专门帮助家庭突发变故的学生。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材料。“
陈晓阳接过文件,眼眶发热。他想起苏晴放在他门口的药品,想起赵家豪二话不说转来的两万块钱,想起林燕学姐帮忙联系的医疗救助...这些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关心他,而他却用固执和骄傲伤害了他们。
“谢谢您,教授。“他站起身,声音哽咽,“我会...好好考虑的。“
走出教学楼,陈晓阳在未名湖边坐了很久。秋日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他掏出手机,翻到苏晴的对话框,手指悬在屏幕上方许久,终于打下一行字:「有空聊聊吗?我想当面道歉。」
消息发出去不到十秒,手机就震动起来:「现在?我在图书馆三楼。」
图书馆三楼靠窗的位置,苏晴正低头看书,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她的侧脸上。陈晓阳站在书架旁,远远望着她,心跳加速。这一个月来,他刻意避开所有可能遇见她的地方,现在却不知如何开口。
苏晴似乎感应到了什么,抬头看见他,微微怔了一下,然后合上书,轻轻指了指旁边的空座位。
“好久不见。“她低声说,声音平静得听不出情绪。
陈晓阳僵硬地坐下:“我...想为上次的事道歉。我不该那样对你发脾气。“
苏晴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脊:“我也有错,应该先问你的意见。“
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陈晓阳注意到苏晴眼下淡淡的黑眼圈,她似乎也瘦了不少。
“阿姨身体好些了吗?“他小心翼翼地问。
“好多了,谢谢关心。“苏晴勉强笑了笑,“你爸爸呢?“
“能拄拐走路了,但干不了重活。“陈晓阳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工地赔了一部分钱,加上赵家豪借的和...你的帮助,债务还得差不多了。“
提到钱的事,气氛又变得微妙起来。苏晴深吸一口气:“晓阳,那笔钱不是施舍。我只是...看不得你那么辛苦。“
“我知道。“陈晓阳抬起头,“周教授今天跟我聊了很多。我一直以为接受帮助就是认输,但其实...我只是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欠人情,害怕还不起,害怕...“他顿了顿,“害怕在你面前永远低人一等。“
苏晴的眼睛瞪大了:“你怎么会这么想?“
“你父亲是著名教授,你家境优越,你...“陈晓阳的声音越来越小,“而我连父亲的医药费都凑不齐。“
苏晴突然抓住他的手,力道大得惊人:“你以为我的人生很完美吗?知道我为什么选择教育学吗?因为我从小到大听到最多的就是'你是苏教授的女儿,应该...'“她模仿着大人的语气,“应该成绩优异,应该举止得体,应该子承父业...“
陈晓阳愣住了,他从未见过苏晴如此激动的样子。
“高中三年,我每天学习到凌晨两点,就为了不辜负'教育家女儿'这个头衔。“苏晴松开他的手,声音低了下来,“大一时我差点抑郁,因为发现自己对学术没那么大热情,更想去一线教书。但我爸...他早就规划好了我读研读博的路线。“
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图书馆的灯自动亮了起来。陈晓阳第一次听苏晴谈起这些,突然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比想象中多得多——都在为父母的期望而活,都被“应该“二字束缚着。
“所以我才那么欣赏你。“苏晴轻声说,“你敢做自己,敢坚持真正重要的东西。“
陈晓阳苦笑:“比如固执地拒绝所有帮助?“
“比如为了父亲可以放下尊严打三份工。“苏晴纠正他,“比如明明那么困难还想着帮助刘强那样的孩子。“
提到刘强,陈晓阳想起那封被泪水打湿的信:“我还没想到办法帮他...“
“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苏晴的眼睛亮了起来,“比如校园募捐?或者联系专门资助乡村学生的基金会?“
“我们“这个词让陈晓阳心头一暖。他看着苏晴充满希望的脸,突然明白了周教授所说的“教育的传承“是什么意思。
接下来的几周,陈晓阳像变了个人。他申请了周教授提到的助学金,重新回到课堂;和苏晴一起组织了为刘强募捐的活动,不仅筹集了学费,还联系到长沙的热心家庭提供住宿帮助;赵家豪也调整了创业团队的架构,允许陈晓阳兼职参与,保留了学业与创业的平衡。
十一月的最后一个周末,陈晓阳带着募捐成果回到青岩镇。刘强和父亲早已在车站等候,看到陈晓阳下车,少年飞奔过来,眼眶通红。
“晓阳哥...我真的能上大学了?“刘强声音发抖。
陈晓阳点点头,转向刘父:“叔叔,这是长沙几位热心人凑的助学金,足够刘强第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后面我们会继续想办法。“
刘父粗糙的手接过信封,嘴唇颤抖:“陈家小子...我...我不知道说啥好...“
“不用说什么。“陈晓阳微笑,“只希望刘强以后有机会,也能帮助下一个孩子。“
当晚,陈晓阳在家中翻出了高中课本和笔记,准备送给刘强。父亲坐在一旁,默默看着他忙碌。
“爸,您觉得我毕业后做什么好?“陈晓阳突然问,“继续读研?还是全职创业?或者...“
父亲放下茶杯:“你想做什么?“
陈晓阳愣住了。他一直在考虑各种现实因素和他人期望,却很少问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我...喜欢教书。“他慢慢说,“特别是看到刘强这样的孩子因为一点帮助就有了希望...“
父亲点点头:“那就去做。别像我,一辈子为口饭吃干不爱干的活。“
回到长沙后,陈晓阳和苏晴的关系恢复如初,甚至更加亲密。他们一起筹备寒假支教活动,经常在图书馆讨论到深夜。有时陈晓阳会送苏晴回宿舍,两人在星空下漫步,聊着各自的童年梦想和未来计划。
十二月底的一个雪夜,陈晓阳收到了刘强的消息:「晓阳哥,我爸同意我上大学了!他说再难也要支持我读完。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陈晓阳把手机递给对面的苏晴看。窗外,雪花静静飘落,覆盖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看,你真的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苏晴轻声说。
陈晓阳摇摇头:“是我们一起改变的。“
苏晴笑了,在台灯温暖的光线下,她的眼睛像星星一样闪亮。陈晓阳突然有种冲动,想告诉她,在他最黑暗的时刻,是想到她的笑容才让他坚持下来。但最终,他只是轻轻碰了碰她的手指,说:“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雪,依旧静静地下着。但在两颗年轻的心里,春天已经悄然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