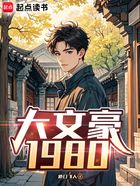
第1章 张盐同志
1980年9月。
苏省金市。
三大火炉之一名副其实,火辣辣的日头毫不留情地释放着炫目滚热的光,供销社门口排队的人都眯着眼。
张盐排在最末尾,手里攥着张肉票,带点破洞的两根筋老头背心,军绿色裤子,劳保胶鞋,让他完美地融进了队伍中,听着排队的人叽叽喳喳:
“听说了吗,马上农业合作社要取消了......”
“唉,票票票......买啥东西啥都要票......啥时候才能不要......”
“这个菜是越来越贵了,米都快三毛一斤了,这谁还吃的起,还不如当农民自己种......”
“听说你们家孩子考上中专了,有出息啦,一毕业就吃国家饭咯......”
“苏联还在阿富汗打来打去......”
......尽管已经是穿越至此第五天,但这些充满了八十年代烙印的交谈还是让他感到一阵荒谬和恍惚。
张盐本是二十一世纪蓝星某211的中文系研究生,正在苦逼地赶着自己的毕业论文——《乔治·桑德斯小说中的后现代解构元素》,某天压力实在太大,就在宿舍买了些零碎吃的,打算过一下烟酒牲的快乐生活,喝了不少牛栏山,本以为能一觉到天明,结果醒来,就到了1980年的金市。
一开始张盐只以为是做梦,毕竟穿越这种事情,除了起点,不常见。
可是随着时间分分秒秒流逝,任凭张盐用什么方法,他再睁开眼睛,仍是一家人挤在一起的逼仄筒子楼,公用的厕所,悬在头顶用电线吊着的老式灯泡,斑驳的墙壁,以及日历上大大的1980年......
几天下来,张盐逐渐接受了这一现实,他穿越到了一个名叫“张盐”的年轻人身上,刚穿越来的时候,别人喊他“张盐”,他还不能立刻反应过来,毕竟他之前有一个用了26年的名字......
“......张盐同志,又在发什么呆呢,买什么?”供销社员洪小巧清脆的声音将张盐从恍惚中拉回到现实。
“买一斤肉,要肥点的。”张盐打量着眼前的这个供销社员,脑中的记忆慢慢复苏。
洪小巧,张盐父亲张慈瑞好朋友洪流的女儿,今年21岁,从“供销班”毕业之后直接分配到了大楼供销社,已经工作两年了。
张盐家和洪小巧家就隔着条马路,两人念一个小学,天天一起上下学,是货真价实的青梅竹马。洪小巧生的漂亮,原来的张盐已经暗自爱慕小巧很久了,洪小巧似乎也喜欢张盐,但由于那个年代的特质,两个人之间始终隔着一层透亮的油纸,互相都看的见,却没有捅破。
洪小巧头发梳成两条麻花辫,是个带点婴儿肥的圆脸,有点像后世的演员谭松韵,笑起来两个小酒窝,穿着蓝色的确良衬衫,不太鼓的胸前佩戴着供销社的徽章,身上一股好闻的雪花膏味。
只不过天太热,尽管供销社里风扇在转,洪小巧细长白皙的脖子也挂着汗。
“知道啦,谢姨昨天和我讲过了,特意给你留了块肥的。”洪小巧笑吟吟地递给张盐一块优质后腿肉。
“好肉都给关系户了......”张盐身后的一个大妈嘟囔着,但也没敢发作,因为墙壁上几个大字分外醒目:
禁止无故殴打顾客。
在八十年代,由于物资匮乏,生产资料拥有者天然享有更大的权利。
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张盐眼观鼻鼻观心当做没听到,伸手去接那块包在报纸里的猪肉,洪小巧却扬手往后一缩,笑道:“连句谢谢都没有啊,张盐同志?”
“谢谢,晚上有空来我们家吃饺子。”
“这还差不多,今天就不去了,我要上夜校,改天吧,记着,你欠我一顿饺子!”
张盐顶着日头回到家,老头衫已经湿透,他干脆脱下来,光着膀子拿起桌子上盛着凉白开的蓝边大海碗,喝了大半碗,这才勉强降去心头的燥热。
坐在比他年龄还大的凳子上,张盐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墙上挂着的全家福。
刚穿越来这几天,当他尝试了几乎所有方式都回不去之后,他经常看“张盐”的全家福暗示自己: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这张波浪边黑白照片是去年照的,前排坐着的是父亲张慈瑞、母亲谢兰和张绛,后排站着的是张材,张米和张盐。
张家是个典型的东国式家庭:大家长,多子女。
父亲张慈瑞,嗜好下棋,国字脸,不苟言笑,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高个,退伍转业干了公安,向阳路派出所所长,话不多,手很黑,张家兄弟小时候没少挨揍。
母亲谢兰,个子不高,在金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下辖的纺织二厂财务科当会计。
张材,大哥,27岁,跟随父亲的脚步当兵去了,眉眼间气质神似《高山下的花环》里的靳开来,经历也像,目前正在交趾前线。
张米,大姐,25岁,随母亲,小个子,脑子很灵光,在纺织二厂做女工,风风火火,已经是领班。
接下来就是张盐,
20岁,一米七五的个子,清瘦且清秀,有张轻易能骗到小姑娘的脸。
原来的张盐初中毕业之后赶着上山下乡的尾巴去苏北农村待了一年,回来后晃荡了两年,去年被谢兰托人安排进了金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下辖的白天鹅天鹅绒织品厂保卫科当干事,和现在的张盐很像,也是个文艺青年,爱小说,爱诗歌,爱音乐,总之,和小布尔乔亚有关系的一切他都爱,常常投稿,次次被拒,在张绛出生之前被张慈瑞打的最多。
张绛,小弟,14岁,上初中,脑子里常有奇思妙想,并经常付诸实践,算是个几把孩子。
张家子女按照柴米油盐酱取名,这是张慈瑞和谢兰的共同想法,张慈瑞1929年生,谢兰1930年生,夫妇二人都经历过战争和运动,自觉能活着就不易,柴米油盐已经弥足珍贵,为了好听,张材和张绛用了谐音,但初衷没变,只求平安是福。
本来还有个二哥张游,但张游是个火爆性子,那几年冲动之下丧命了,张游生前最爱吃饺子,今天是张游的阴寿,因此谢兰早早和洪小巧交代,要留一块好肉。
门外传来响动,母亲谢兰和大姐张米拎着菜回了家。
“张盐,叫你把肉放水里加点盐泡着,脑子呢?”谢兰一进厨房就开始嚷嚷,随即麻利地擀面,剁肉,调馅......
张米本来想进厨房帮忙的,被谢兰赶出来了,说今天这顿饭只能她做。
“妈,我饿了,今天吃饺子啊,太好了。”张绛背着个斜挎书包,一进家门就把包往旁边一甩,直奔厨房。
饺子下锅之前,张慈瑞回来了,身着白色七八式警服,胳膊夹着大檐帽,手里拎着瓶挹江大曲。
饭桌上坐了五个人,摆了七碟饺子。
素什锦,盐水鸭,炒豆芽,红烧肉圆,是很丰盛的一餐,也都是二哥张游爱吃的。
张绛已经按捺不住筷子。
张慈瑞拧开挹江大曲,给自己倒了一杯,又在二哥张游的空位置前倒了一杯。
张慈瑞抿了口酒,沉默几秒,开口道:“都吃吧。”
“......爸”张盐这几天喊爸妈总有些磕巴,搞得谢兰还以为他舌头出了问题。
“......我陪您喝点吧。”
今天这顿饭是为了纪念二哥的阴寿。
张盐也想和原来的世界做个告别,他明确地知道,已经回不去了......
张慈瑞和张盐把这瓶挹江大曲喝完了,两人酒量都还行,但半斤下肚,还是有些微醺。
张盐回到自己的房间——张家是三室格局,这在当时已经颇为难得。
张材和张游还在的时候,张慈瑞谢兰两人一间,四兄弟挤一间,张米一间。现在少了两个人,已经结婚的姐姐张米吃完饭回了自己家,张盐就和张绛各自就拥有了一间房。
张盐的房间约莫有十来个平方,一张铺凉席的小床,一张压着玻璃的旧书桌,一个装满书的书柜,书柜里有《鲁迅全集》,有《围城》,有《青春之歌》,有《红与黑》,有《安娜·卡列尼娜》,有《外国文艺》,有《今天》......还有满满的退稿信。
这些退稿信,寄回的单位有《当代》《十月》《小说家》《长城》《人民文学》《收获》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也有《鄂尔多斯文艺》这些地方性新刊物......
原来的张盐属于是得了余桦的病,没有余桦的命。
张盐看了原来张盐写的东西,只能说一言难尽,充斥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自以为是的先锋以及要溢出纸张的自我感动,最重要的是,原来的张盐常常兴致勃勃地开头,然后憋个中间,最后草草结尾。说人话就是写不下去硬要写。
也许是喝了酒,张盐翻阅着这些装帧简单书页泛黄的书,看着那些熟悉的铅字,脑子翻江倒海:
这是1980年的东国,路远还没有写出《人生》,余桦还在口腔科学习,管莫言还没有发表过作品,苏瞳刚刚考进京城师范大学,蚕雪还在当工人......
或许,我也可以写点东西......
一首手抄的诗从张盐捧着的书中滑落,
是赵振开的《走吧》
走吧
走吧,
落叶吹进深谷,
歌声却没有归宿。
走吧,
冰上的月光,
已从河面上溢出。
走吧,
眼睛望着同一片天空,
心敲击着暮色的鼓。
走吧,
我们没有失去记忆,
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
走吧,
路呵路,
飘满了红罂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