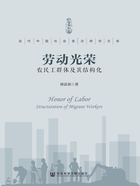
研究问题和写作结构
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算起,农民工的数量已经持续增加了四十多年。这就是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过程,即在一定历史时期以打工生活方式为显著特征的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占据比较稳定的比例的过程和现象。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农民工群体为什么会长期存在而且不断扩大呢?或者说,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发生机制是什么呢?这就是本研究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研究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是我国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发展道路的一个显著特征。理解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及其发生机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而且,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过程可以为研究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机理提供重要契机。一般而言,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我国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力都是由国家集中组织和管理的,我国还不存在严格的劳动力市场。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也依赖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整体变迁。研究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提供经验基础。此外,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采取了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其中,国家和市场的互动尤其重要。研究农民工群体结构化过程中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不仅为研究工人政治提供了机会,而且为研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机会。
研究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机制也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如前所述,农民工群体产生以来,国家便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来解决农民工问题、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和农民工带来的社会问题。从农民工的生活状态来说,他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包括工资较低、家庭分离、留守儿童、住宿条件不善、工作环境恶劣等。帮助农民工提高工资、保障农民工就业、维护农民工权益、改善农民工境遇等都需要对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机制进行客观分析,从而制定出更加有效和符合农民工愿望的政策。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我国的社会稳定。从我国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是不可避免的政策导向。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之后,推进我国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保障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序进行,实现产业升级和改善消费方式,都需要对农民工群体采取更加合理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制定也离不开对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机制进行客观分析。
为了说明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机制,本书将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是总论部分。第一章主要介绍农民工的界定和简史,并用“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概念来描述当前我国农民工群体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书的核心研究问题:农民工群体为什么会长期存在而且不断扩大?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机制是什么?第二章将介绍本研究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首先分析关于当前农民工研究的三大范式,包括移民范式、城市化范式和阶级形成范式,并认为现有的三大范式都不足以描述和解释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过程及其机制。在此基础上,认为劳动体制范式可以更加综合地对农民工现象所涉及的制度、政策、动机、态度和行为进行客观分析,从而解释农民工群体的长期存在和不断扩大,也可以为城市化问题和劳动力问题提供理论和经验基础。但是当前的劳动体制范式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因此第二章还将对劳动体制范式进行充实和发展。在介绍了理论视角之后,还将介绍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将阐释性定性研究和批判性定性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更加综合地考察结构制度和动机态度之间的互动机制。
本书的第二部分由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组成,主要是从微观层次上对农民工的客观生存状态和主观动机态度进行阐释性分析。第三章主要关注农民工的打工动机,认为当前的两种主流理论——“永久迁移理论”和“家庭策略理论”——都没有全面分析农民工的打工动机。然后,在梳理“迁移理论”和“迁移动机理论”的基础上,基于经验调查提出了一个农民工打工动机的理想类型。调查表明,农民工的打工动机具有层次性特征。在这个层次性的动机结构中,农民工打工的深层动机在地理取向上分为城市取向和农村取向两种类型,在社会取向上分为个体取向和集体取向两种类型。在动机分层结构中,不同层次的动机取向存在复杂的“目的—手段”关系。但是,总体而言,根据动机的地理取向和社会取向,农民工的打工动机具有个体荣誉、个体前途、居家需求和家庭发展四种理想类型。而且,在打工过程中,农民工的打工动机也会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第四章考察农民工对待打工生活方式的态度,因为农民工的打工动机不同于他们对待打工生活的态度。农民工的打工动机和预期是他们打工的目的,而打工生活方式则是他们实现那些目的的手段。就农民工对待打工生活方式的态度而言,虽然打工生活能否满足他们的打工动机和预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持有相同打工动机的农民工可能发展出不同的生活态度;而且,对于各种取向的打工动机而言,这种情况都存在。造成农民工对打工生活方式持有不同态度的另外一个影响因素是他们对于替代方案的认识:当农民工有打工的替代方案而且替代方案实施的可能性很大的时候,农民工对于打工生活方式的拒绝态度会更强烈,接纳态度也就更微弱。反之,当农民工没有打工的替代方案或者实施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很小的时候,他们对于打工生活方式的接纳态度会更强烈,拒绝态度也就更微弱。此外,在打工的过程中,农民工对待打工生活方式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根据他们对待打工生活方式接纳程度的高低,农民工在打工过程中可能会经历乐观化和悲观化两种过程。乐观化的过程是农民工对打工生活方式的接纳程度升高的过程;而悲观化的过程是农民工对打工生活方式的接纳程度降低的过程。乐观化和悲观化过程背后的双重逻辑就是动机合法化机制、替代方案可能性机制和打工生活选择性机制。动机合法化机制是指动机能否为打工生活提供动力支持。替代方案可能性机制是指农民工对于替代方案是否存在和实施是否可能的认识会影响他们对打工生活方式的接纳态度。打工生活选择性机制是指打工生活内部的多样选择可能会强化他们对打工生活方式的接纳程度,因为他们会通过选择不同的行业和工作地点来满足他们的预期和需求。第五章则在生活方式理论的基础上对农民工的打工动机和对待打工生活方式的态度进行进一步解释,即用农民工最直接的客观生存状态来解释他们的主观动机态度。他们的动机态度和生存状态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他们的动机态度是由生存状态所形塑的,而这种被形塑的动机态度又成为他们生活在那种生存状态中的主观基础。因此本研究用“同构性”来说明客观生存状态与主观动机态度之间的关系模式,并用“互构”来描述两者之间的互动过程。
本书第三部分由第六章到第九章组成,对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制度因素进行分析。第二部分主要是在微观层次上分析了农民工的主观动机态度和客观生存状态及其“同构性”和“互构过程”,如果客观的生存状态形塑了主观的动机态度,那么这些生存状态又是如何造成的呢?如果客观的生存状态和主观的动机态度之间存在“互构过程”和“同构性”,那么这种“互构”和“同构”的价值取向和认知框架又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第三部分致力于分析影响农民工生存状态、价值取向和认知框架的制度因素。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分析了农村居民“流动”行为的制度性影响因素。简而言之,农村生产生活的变迁、人口流动控制的放松和城镇就业机会的增加是刺激农村居民流动的三种主要制度性因素,这些制度性因素为农村居民的流动提供了“动力”、“拉力”和条件。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赋予了农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自主性。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重组,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因此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农村居民外出务工提供了客观条件。农村家庭生活消费的独立强化了农村居民的家庭意识和家庭认同;农村社会关系的变迁提高和增加了农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这都为农村居民外出务工提供了内在动力。城镇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的重组改革、外资企业的兴起发展,都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为农村居民的流动提供了“拉力”和客观条件。最后,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人口流动控制——也逐渐松动。虽然户籍制度仍然被用来对流动人口进行控制和管理,但是农村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和城镇经济发展的需求使得对流动人口的控制和管理政策形同虚设,农村居民获得了实质上的流动权利,这也为农村居民的流动提供了客观条件。但是,农民工的打工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流动”,还是一种“不完全迁移”,甚至是一种“持续流动”或“循环流动”。第八章和第九章集中考察农民工“不完全迁移”或“持续流动”的制度性影响因素。户籍价值变迁及其产生的居民地位分化、城市非正规就业和市场文化是影响农民工“不完全迁移”和“持续流动”的主要制度性因素。其中户籍价值变迁及其产生的居民地位分化强化了农民工的农村认同和地域认同,而这种身份认同又使得他们能够接受打工生活方式,而没有采取激烈的反抗行为。城市非正规就业不仅影响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而且强化了农民工所持有的“市场逻辑”,使得他们认为他们是“低级工人”,而大学生和城市居民是“高级工人”,这种“市场逻辑”也使得农民工接受了他们的打工生活方式。
作为总结,第十章在我国整体的实践性发展进程中考察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过程。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是一个过程,因此必须放在我国实践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而不能像“三元社会结构理论”那样采用静态的眼光看待农民工现象和我国的整体发展趋势。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也说明,农民工群体已经存在了四十多年,而且还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带有理想色彩的“社会转型理论”也不能实践性地把握农民工结构化的现实和我国整体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说明我国的发展道路是一种“实践性发展”。同时,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发展和前途也必须放在我国实践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具体而言,我国的实践性发展经历了国家总体控制、国家放权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三个阶段。国家总体控制是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背景,国家放权改革是农民工群体结构化的过程,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逐步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愿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分清轻重缓急,着重解决好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三项工作,并在这个过程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概而言之,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包括:(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民工群体呈现了结构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占据着比较稳定的比例;(2)当前关于农民工的主流研究范式——移民范式、城市化范式、阶级形成范式——都不足以回答“我国农民工群体何以结构化”这个核心问题,而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劳动体制范式则可以综合性地对农民工现象所涉及的制度、政策、动机、态度和行为进行客观分析,从而解释农民工群体的长期存在和不断扩大,也可以为城市化问题和劳动力问题提供新视角;(3)农民工的打工动机呈现多层模式,但是不同的生产和生活状态使得他们具有不同的深层动机,包括个体荣誉、个体前途、居家需求和家庭发展等;(4)农民工对待打工生活的态度也存在差异,主要取决于打工能否满足他们的需要、打工替代方案的可能性、打工生活的选择性;(5)根据他们的打工动机和生活态度,农民工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冒险型、乐观型、工具型和退出型;(6)农民工的动机态度受生活状态的影响,而他们的生活状态又受到宏观制度安排的影响,主要包括农村劳动体制的变迁和农村家庭自主性的获得、户籍制度变迁和人口流动控制的持续放松、居民地位的分化、城市劳动体制的变迁和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市场文化;(7)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化是我国实践性发展进程的产物,也必将在实践性发展进程中消亡。
[1] 老泰是作者的一个研究个案。为了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本研究遵循保密性原则,使用化名来称呼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