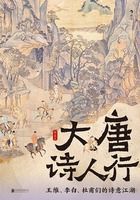
第4章 英主与心魔
当然,没有人能够否认,李世民是一代英主。
尤其是武功方面,即位后仅三年半时间,他就派大将李靖、李勣(即李世勣,因避讳而改名)灭掉了东突厥汗国。北方最大的威胁解除了,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包括农耕与游牧民族在内的天下人共同的皇帝。
贞观四年(630)夏天,李靖将突厥颉利可汗押至长安。李世民将颉利可汗大骂一通,颉利“哭谢而退”。
接下来,史书记下了极具纪念性的一幕:
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
当时,李渊早已退位当了太上皇,但听说这个好消息后,他仍然在凌烟阁摆酒庆贺。李渊弹琵琶,李世民跳舞,用一场盛大的狂欢,来洗刷被突厥欺辱的往事,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随后,唐朝又派兵攻占西域诸国,势力直达葱岭以西,与波斯、印度相接。李世民的“天可汗”名副其实。
然而,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史书,又会发现李世民一直生活在“两重心魔”之下。而这两重心魔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李世民成了一个诗人、一个偶像。
第一重心魔是隋炀帝。
作为皇帝的隋炀帝无疑是个失败者,但作为诗人,他很有才华。李世民并不讳言自己欣赏这位表叔的诗。他曾在朝堂上公开赞扬杨广的诗,说:“朕看隋炀帝的文集,看那些言辞语句,宛若听到了尧舜之言。可他为什么总干些桀纣之事呢?”
不妨先看两首杨广的诗: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
——杨广《野望》
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皋麦陇送余秋。渌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跃紫骝。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清歌乐戏州。
——杨广《江都宫乐歌》
一首五言,一首七言。如果不署名的话,人们大概率会认为这是唐代诗人的杰作。
杨广的诗,既有北方的刚健豪迈,又有江南的婉媚空灵,且将二者融合为一。
这是文学才华的体现,也与杨广的成长背景有关。他是一个既懂生活,又有权力的人。他十三岁就被封为晋王、并州总管,二十岁率军南下,扫平陈朝。也是在十三岁时,他娶了梁朝皇室后裔萧氏为妻。这种结合,当然首先是一种政治婚姻。杨坚为儿子娶萧氏为妻,是为了加强对长江沿岸的控制,而文化只是不经意间的副产品。因为这位萧妃的曾祖父,正是编选《昭明文选》《文章英华》的梁武帝长子萧统,乃执掌南朝文学法度之人。萧妃不仅有教养和文采,还是杨广的终身伴侣和红颜知己。在她的影响下,杨广深深懂得了南朝的审美,甚至学会了吴语。南北方不同的风格,在杨广身上产生了化学反应。
另外,杨广还有一项特殊的“禀赋”——他是一个性格暴虐的不肖子。即位之后,他便随心所欲地更改父亲所订立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文风更不在话下。他将杨坚所定的审美标准抛至九霄云外,而且以他动辄诛杀高官的作风,没有哪个大臣敢对他的写作风格指手画脚。
结果便是,杨广成了宫体诗的继承者和改造者,在当时独树一帜。
后人看到的是,杨广作品的风格和水平,都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
在诗歌写作方面,杨广堪称李世民的偶像。而将李世民的诗和杨广的放在一起对比,结果总是残酷的。
虽然李世民对南朝审美也深度沉迷,可他对江南并无多少直观体验。他的战场一直都在江北,江南的大片土地,是他的堂兄李孝恭率领李靖打下来的。而他也缺乏杨广那样的“诗人气质”。甚至于,李世民二十三岁建立文学馆之前,都没有读过多少书。至于安心读书、写诗,更要到当皇帝之后了。
总之,单就文学领域而言,李世民比杨广是全面落后的。唯一能与之媲美的是豪情,可是这一点,李世民还不会利用。这不能不让他倍感焦虑。
他又能怎么办呢?
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寒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钲。绝漠干戈戢,车徒振原隰。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
——李世民《饮马长城窟行》
这首诗的题目来自汉乐府,历史上有不少相同题目的诗。光看李世民这一首的话,即便不能说好,也并不算差。
然而,假如读过杨广此前写的一首《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就会觉得李世民这首诗似曾相识,即使不能说抄袭,至少也算借鉴模仿。
不仅如此,在李世民不少诗中,都能看见杨广的影子。
比如,杨广曾写过一首诗送给大臣杨素,其中有句子是:“疾风知劲草,世乱有诚臣。”而李世民后来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
——李世民《赐萧瑀》
当然,这样做的皇帝,绝非李世民自己,后世还有好几个。
杨广虽没有抄袭嫌疑,但据说曾因嫉妒而杀人。此前,曾先后在北齐、北周和隋朝做官的老诗人薛道衡,有一首描写思妇寂寞心情的诗,其中两句“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传诵一时。杨广看后很嫉妒,就找了个借口逼其自尽。薛道衡死前,杨广还说风凉话:“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薛道衡之子薛收,后来成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为推翻隋朝、平定天下出了一份力。他的子孙后代也成为大唐文人中的重要一脉。
另一重心魔是玄武门之变。
在这场政变中,李世民大获全胜,不仅斩杀了自己的两位亲兄弟,还把四弟李元吉的王妃杨氏纳为己有。于是,他与杨广又多了一重亲戚关系。杨广是他的表叔,也是岳父。
这里必须说的是,唐朝的皇室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汉人血统。虽然他们自称陇西李氏一脉,可追溯到汉代名将李广,但史书能查询到的是,他们源于东部赵郡李氏中的“破落户”,其先祖中有两个人名叫“李初古拔”“李买得”,可能是鲜卑族。他们的后人与汉人联姻,再往后又与突厥贵族独孤信联姻。而这位独孤信堪称“史上最牛岳父”,他有三个女儿被封或追封为皇后,其中两位嫁给一国之君,另一位生下了开国之君。长女嫁给了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嫁给了李渊的父亲李昞(bǐng),七女嫁给了隋文帝杨坚。而李世民的母亲窦皇后也有鲜卑血统,他妻子长孙皇后更是鲜卑贵族。所以,整个大唐皇室都有着“汉—鲜卑—突厥”血统。
这种说法虽然一直被大唐皇室刻意隐藏,但从不断涌现的“兄纳弟媳”“子承父妻”“父纳子妻”等匪夷所思的做法里,仍能看到游牧民族的习惯。
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登上了皇位,但亲兄弟的鲜血也浇筑成一个铁一样的血迷宫,让他困在里面夜夜不得安睡。
穿过史册,世人看到的李世民光芒万丈。这光芒一半来自他的励精图治,另一半则来自他所营造的“人设”。他希望用这种光芒,驱散玄武门的那抹血色,殊不知血色早已入骨,也将在大唐皇室的基因中代代传承。
其实,关于李世民是实力派还是偶像派,历史学者们向来有分歧。综合而言,他就是一个一心走偶像路线的实力派,他与他的朝臣们共同上演的贞观大戏,成功入选了中国古代帝王政治的教科书。
这两重心魔又交织在一起。比如,李世民与杨广都是次子,又都通过害死兄长而上位。李世民非常担心世人把自己与杨广联系在一起。为了消除心魔,他采取了两大行动。
其一,修史。
历史是有力量的。唐朝之前各个朝代的史书,虽然也是在皇帝主持下,由史官利用国家档案编写而成,但其仍然属于史官私家著作的范畴。但到了唐朝,尤其是唐太宗时期,成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修史成为一项官方任务。权力总是不拘一格的。人只要大权在握,就会把手伸向自己想要的一切。在过去,史官的一支笔有着极大约束力,青史的监督功能不容忽视,然而到了唐朝,事情开始起变化。从这一刻起,私家史变成了官方史。史馆不仅负责编修前朝史,也要随时编纂当代史。
在新组建的修史班子里,房玄龄、魏徵是主要负责人。虽然玄武门之变时二人所属阵营不同,但均为重要当事人,也最清楚李世民的底线。从贞观三年(629)开始至贞观十年(636)结束,梁、陈、北齐、周和隋等各朝(国)史书先后完成。在这些史书中,隋炀帝杨广被写成了一个彻底的反面典型。李建成、李元吉在建立大唐过程中的作用也被极大贬低,二人的形象被定性为“建成残忍”“元吉凶狂”“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
甚至连唐高祖李渊“建立唐王朝的功绩(也)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在相关史书完成的前一年,李渊已去世,不会知道儿子将怎样涂抹他的功劳簿。
今天,我们看到的史书写着:李世民从十九岁开始,就成为建立大唐王朝的总策划,而大唐的开国皇帝李渊却总是浑浑噩噩、坐享其成。这在史上的开国之君中,可谓空前绝后的“奇观”。直至现在,学者们想为李渊写一本靠谱的传记,仍千难万难,因为大部分史料都已被他儿子的大臣所修改。当正史变得不“正”,这位开国之君注定只能面目模糊。
即便如此,李世民仍然对玄武门事变的记述不放心,与性格耿介的史官褚遂良不断发生摩擦。
其二,纳谏。
在后人印象中,纳谏是贞观之治中最鲜活的场景。魏徵为了天下百姓,一次次以劝谏的形式挑战皇帝的底线,而皇帝也总是能够包容,从善如流。这是一种被后世文人奉为“君臣共治”的理想模式。
这种场景极富感召力。这是李世民胸怀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他的胸怀如海,外化为整个朝廷的气度,甚至为大唐气象奠定了基础。没有人可以否认,他是古来少有的明君。
但也要看到,李世民绝非完人。比如,他属于较为典型的表演型人格,有时候纳谏只是为了表演,而魏徵也在紧密配合。那一刻,两个人都是“演员”,相互搭档来制造美名。在这场大戏中,如果说唐太宗是最佳男主角的话,魏徵就是最佳男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最佳台词,铜镜则是最佳道具。
这场大戏的指向仍然是隋炀帝。因为在世人印象中,隋炀帝已成为一个不听劝谏、嗜杀成性的暴君代名词,李世民反其道而行之,更容易打造明君“人设”。
贞观六年(632),李世民导演了一幕著名的盛世大秀。史书记载:
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之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
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
李世民让死囚们回家,命其秋后回来领死,结果这些人全部准时回来。于是,李世民赦免了他们。这被当成皇帝感化罪犯的典型案例,但后世的欧阳修对此非常怀疑,认为君子都不一定会按约定去受死,何况是全部死囚?这实在太可疑了。明清时的大儒王夫之更是一针见血:“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争夸者,必其诈也。”
当然,任何人也不能否认,魏徵富有勇气,他所从事的是一项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而在他狠怼李世民的时候,长孙皇后也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这位皇后出身将门,知大略、识大体,她与李世民是史上少有的著名而不奇葩的皇帝夫妻。
在玄武门之变之前,她曾亲自上场,激励将士,“左右莫不感激”。李世民即位后,长孙皇后衣带上时刻悬挂毒药,表示一旦李世民驾崩,她便服毒自尽,“誓死不当吕后”。
一次,李世民退朝回宫,嘴里念叨:一定要杀了那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忙问原因,李世民恨恨地说,魏徵上朝时公然让自己下不了台。长孙皇后听后默默回到内室,换上皇后朝服向李世民行礼,她说:“妾闻主明臣直。魏徵犯颜直谏,说明陛下是有道明君,此等幸事,岂能不郑重道贺?”这样的仪式感和恭维语,使李世民转怒为喜,成功保护了魏徵。
长孙皇后也有诗传世:
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长孙皇后《春游曲》
囿于当时的审美,这位将门虎女、一代贤后的诗,也呈现出一派香艳气息。更令人叹惋的是,她虽比李世民小两岁,却比他早去世了十三年。假如她能再长寿一点,“贞观之治”的成色或许能更好一些。
长孙皇后去世之后,李世民陷入了悲伤,直至第二年仍郁郁寡欢。为了能让皇帝开心一点儿,朝臣们不断举荐出身名门的少女入宫。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被送入宫闱。在此之前,她的父亲早已过世,她和母亲被父亲原配的子女赶出家门,前途一片黯淡。
入宫后,女孩的才华开始展露,并成功吸引了皇帝的注意。因她姓武,李世民为其赐号“武媚”。
这个女孩与李世民之间,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她入宫不久,李世民得了一匹烈马,名为“狮子骢”,此马雄健俊逸,但脾气暴烈,无人能够驯服。此时,女孩挺身而出:
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檛(zhuā)、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
作为史上著名的爱马人士,李世民当然不允许她这样粗暴对待自己的宝马。但他还是很惊奇,这个女孩的豪气,颇对他的脾气。但他不会知道,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个女孩会给他的江山和家族带来怎样的浩劫。
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大致可分前后两段。
前十年,他与大臣共同努力,开门纳谏,整个朝廷充满了新鲜的空气。同时,他还主持编纂律令,开办学校,完善军制等。这些制度虽然整体上未脱隋朝的窠臼,但成功让整个国家稳定下来。
而后半段时间,李世民有些累了,魏徵早早觉察出这种倾向,写了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希望皇帝体恤民力,在朝政上多用点心,但并未收到太多实效。
而且,在此后的岁月里,魏徵与李世民这段佳话也渐渐变得“不佳”。
魏徵死后,他推荐的侯君集造了反、杜正伦被罢免。而让李世民更恼火的是,他发现魏徵竟然把生前的谏言留了一份底本,还拿给了史官褚遂良看。这就等于为给自己争脸,而让皇帝没脸了。
李世民一气之下,取消了他最小的女儿衡山公主与魏徵长子的婚约,还下旨把魏徵的碑文磨掉,墓碑推倒。
贞观十九年(645),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想再次证明自己比隋炀帝更强。然而,这次战争的结果,是将士死伤两千人,战马损失十之七八。他深感后悔,长叹:“如果魏徵还活着,他是不会让我打这场仗的。”于是,重新祭祀魏徵,为他立碑。
李世民还写了一首诗,以悼念一位名叫姜确的心腹爱将:
凿门初奉卫,伏节始临戎。振鳞方跃浪,骋翼正凌风。未展六骑术,先亏一篑功。防身不足智,徇命有余忠。悲骖嘶向路,哀笳咽远空。凄凉大树下,流悼满深衷。
——李世民《五言悼姜确》
老了的战神按剑良久,迎风洒泪,如此一幕令人黯然神伤。
而李世民背后,是广阔辽远的大唐版图。在这片逐渐恢复生机的土地上,他的剑与诗都将流传下去,并作为一种传统,跨越千年,让无数士人拼尽一生的力气,苦苦求索。
又过了四年,李世民因病晏驾,庙号“太宗”,谥号“文皇帝”,后加谥“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葬于昭陵。
允文允武,十全十美。他可以放心闭眼了。
一代英主名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