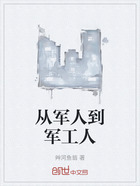
第23章 新兵训练
1978年3月12日晚,载满新兵的列军到达SC省NJ市的号志口火车站(内江东站)。火车站里早已停着一排接站的军车,一辆辆军车很快把我们送到沱江河畔的内江谢家坝新兵营。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 13军,对我来说,那是特别亲切的存在。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它的军部就驻扎在重庆,一直都在我身边。打我小时候起,每次进城,都得从杨家坪坐3路公交电车去两路口。而位于市中区峨岭的第13军军部大门,正是3路公交电车的必经之地。那时候,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少年,每次路过,看着军部大门,心里对那些穿着绿军装的军人,满是崇拜。
眼下,我特别幸运,真就来到了这支光荣的部队,成为了一名有抱负和志向的中国军人,总算是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从军报国”的心愿。
谢家坝位于内江城东的沱江岸边,这里原修建有一个招待所,与内江党校相邻。后来招待所改建为陆军第13军第39师师部驻地。整个营区包括一个很大的院落及周边的小山峦上的营房,主要单位包括师三大机关、通讯营、警卫连、侦查连、防化连、汽车连和修理所、小车班、卫生队、文工团以及随军家属区域。部队大院里绿树成荫,办公大楼、大礼堂等高大的建筑与一幢幢幽静的小洋楼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河岸一片围墙里面,还有一个灯光篮球场,有一个由游泳池改建的军需仓库。机关大院的左侧有一座小山岗,小山上是师直属队部分部队的住地。
新兵营的营房,位于师部大院围墙外的一块平坝上,与部队大院大门旁边的警卫连营房相对。新兵营的营房前面有一个大操场,操场外是整齐的水田,背后坡下是沱江岸边的一大片河滩。
其它省份的新兵有的在我们之前已经到达,操场上黑压压的一片,千篇一律洋溢着青春热情的新兵笑脸,以及一张张笑脸背后迥然不同的来历与抱负。
哨声响起来了,口令之后是一个没有听清楚什么级别的干部训话。训话之后在带兵干部的组织下进行了分班,我被分到新兵连11班。
11班里有10个新兵和一个老兵班长共11个人,分别来自四川、河南、云南和重庆等省市,其中有三个是下乡知青。班长是来自师直属队独立通讯营无线电连的报务兵。他来自四川,军龄三年,个子不高,性格有点婆婆妈妈,是个心细如麻的人。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新战友,生活背景、风俗习惯、性格特点各不相同,南腔北调之声不绝于耳。对这些大都未曾离开过家乡的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来说,如今初次出门在外,老乡之间,口音相近,习俗相仿,感到比较亲切,自然交往密切。从新兵连开始我就深有体会:部队里大局观念重,老乡观念也重。
新兵连的干部是从师直属队各部队临时抽调的,他们带着分给自己的队伍,来到早已分配好的营房,吃饭后打好地铺,已经是深夜1点多钟了。
夜已经很深了,窗外十分宁静,在这远离家乡的异乡土地,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我向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兴奋得无法入眠。
崭新的军用棉被盖在身上非常暖和,我听见身旁的地铺上不断有人在翻身,显然有新兵战友与我一样夜不能寐。我翻来覆去,胡思乱想,起身上厕所时,看到窗台上放有一个手电筒,便悄悄拿来,趴在被窝里,借着手电微弱的光亮,写下了入伍后的第一篇日记。这篇日记是我学习写的一首题为“从知青到军人”的格律诗:“下乡插队黄瓜山,年少轻狂性率真。瘦影晨耕挥锄早,茅庐读书夜已深。知青岁月空抛掷,壮志襟怀枉费辰。回首往昔心浩叹,且期军营梦逢春。”
第二天开始新兵培训。上午的第一堂课,是通信营的教导员引经据典、谈古论今,讲了我军的性质和使命。课后还组织新兵进行了讨论,引导大家交流学习体会,谈感想、谈理想,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下午还是政治学习,由工兵营的教导员来给全体新兵上课,给我们讲军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服役的陆军第13军,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31军之一部,参加了创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万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参加了建立以太行地区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参加了挺进中原,开创豫西解放区。1949年2月,第4纵队在HEN省郾城县黄阁村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下辖第37师、第38师和第39师,隶属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在兵团司令员陈赓指挥下,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粤桂边追歼战和滇南战役。
建国后,第13军长期驻守云南,执行剿匪建政、屯垦戌边、建设边防等任务。1950年参加了抗法援越斗争;1960年11月至1961年2月发起了中缅边界勘界警卫作战,深入到缅甸、老挝、泰国交界的“金三角”腹地,摧枯拉朽打击逃缅国民党残军;1964年8月,美国入侵越南,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第13军又参加了抗美援老、抗美援越斗争,为我军热带山岳丛林地作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还为越南人民军训练了两个师又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后来划归第13军的第149师原为第18军的第52师,参加过1959年的XZ平叛和1962年的对印自卫还击战。第13军是建国后我军出国作战最多的部队,成为威震敌胆的“山地丛林之虎”。
1968年12月,第13军调防四川重庆,接收54军营区,代号为56005部队,隶属成都军区,先后担任战备执勤和训练、国防施工和营建施工、三支两军、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和抢险救灾等任务。
新战士们听得如痴如醉,心中充满了敬佩与自豪。后来,第13军于1985年12月改编为第13集团军,代号由56005部队改为77100部队,隶属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为全机械化部队,是全军中最擅长山地、高原、热带丛林作战的甲类集团军,为解放军快速反应部队之一。2016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大军区撤销,成立五大战区,第13集团军划归西部战区陆军。2017年4月,以陆军第13集团军为基础,调整组建陆军第77集团军,军部驻地从CQ市移防SC省CD市崇州市。
随后开始了新兵训练。
新兵训练听上去似乎简单,做起来颇为紧张。归纳起来为:白天的训练大致是出门练队列,进屋练内务;晚上重点学条例。
当清晨军营嘹亮的军号催促我们起了床,一天的训练就从出早操开始:一二一,一二一,我们跟着值班排长的口令,围着大操场跑完步。早饭后一般以班为单位进行队列训练,班长发出:“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正步走”等等口令,队列中的新兵们按口令指示操作。别小看这几个单调枯燥的动作,据说可以外塑军姿,内练精气神。
队伍条例对军人齐步走和正步走的步频和步幅是有具体规定的。齐步走还好一点,特别是练正步,先要练分解动作,按“一、二、停”的口令做出一步一动和一步两动的分解动作,那个金鸡独立的姿势,我们从开始一站30分钟到后来站两、三个小时。站的时间长了,又困又累,有的新兵腿变得僵直生硬,有的累得抽了筋。有时思想稍不集中,就会有人听错口令,搞得散漫惯了的新兵们狼狈不堪。
趁课间休息的空闲,有人松开腰间的武装带,揉着又红又肿的腿肚子,免不了私下抱怨几句。也有调皮的家伙,背后偷偷骂严格要求我们的老兵班长“宝器”之类怪话,大家对这类一派胡言还纷纷附和。但集合起来后没人敢偷奸耍滑,为了尽快实现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大家都咬牙坚持。
军姿训练结束后,新兵们都有收获,一个个坐立时目不斜视,行走时腰板挻直,做事也稳重多了。
每天晚上集合晚点名,要对当天的训练进行点评,然后学唱军歌,组织学习条例。每周还要抽一个晚上上一次大课:防化连的指导员给我们讲过军队铁的纪律和军人必备的素质;高炮连的指导员给我们讲过形势和任务。
每个周末都要组织一次师直属单位部队在师部大礼堂看电影。在部队,凡事都要有集体观念,要求统一、服从、令行禁止。集体生活的新鲜、剌激,使我们每一天都在接受新的东西,每一天都在进步。
军队肩负着保卫祖国,反击侵略的重任,必须对突发事件保持高度灵敏的反应能力,做好时刻打仗的准备。除了日常的军事训练之外,定期开展军事演习、各级拉练以及平常进行紧急集合训练,就成为保持战斗力的基本手段。
我在部队的第一次紧急集合训练,就是在新兵连经历的,是夜间3公里越野。那时的我们刚到部队,普遍反应不敏捷,手忙脚乱出尽了洋相。
那天是到新兵连的第二个星期天,新兵们白天可以在营区内自由活动。听老兵说师部大院家属区附近有个军人服务社,九点钟吃饭后,同班的几个新兵来到军人服务社。军人服务社面积不大,是一个很小的杂货铺子,售货员是部队家属,卖一些糕点糖果和烟酒,牙膏肥皂洗衣粉,还有衣服布匹等日用百货,我们按需要添置了日用品;有的新兵到浴室洗了澡,洗了衣服;有的在宿舍写家信。请假外出的,下午四点前就急急忙忙回队销假。晚饭后大家有说有笑,心情很是放松。晚上八点的班务会后,正常洗漱睡觉,也没有谁通知等会有训练安排。
凌晨12点10分,一阵“嘀嘀嘀嘀”尖利剌耳的长哨声把睡得正香的我们吹醒。老兵班长扯起喉咙厉声喝令提示,并守在门口的开关旁边,不准我们开灯。
我条件反射似的弹了起来,地铺上的新战士们已经乱成一团。大家睡眼惺忪地翻身爬起,摸黑找衣服穿好,然后打背包,背水壶,带挎包,扎腰带,在老兵班长“恶狠狠”的催促中,一个个衣冠不整冲出营房。
全连在操场上东倒西歪地整队完毕,连长看都不看七零八落的队伍,也不多说,直接下达口令开跑。队伍就稀里糊涂地跟着他跑出营区,爬了一个长缓坡,拐了两个弯,上了漆黑寂静的公路。
我的军帽在黑暗中不知被谁拿错了,胡乱抓了一顶别人的又有点小。鞋带来不及系上,腰带也松松垮垮,根本迈不开大步。背包本来就没有打紧,出了营区大门不久就散了,我一手挟着被子、一手提着裤子,和一群帽子没戴的、衣服穿反的、鞋子跑掉的新兵们,喘着粗气拚命追赶,还是与大部队越拉越远。
当我们落在后面的一拨人呼吸急促的勉强跑完全程,陆陆续续回到操场,全连都在等着我们十来个掉队的人。各班的老兵班长开始检查新兵们携带物品情况,先回来的人也是一样的丢盔弃甲,还有一个因为小腿痉挛而坐到了地上。
连长照例训了一番话。开始我和掉队的人一样,心里作好了挨批评的准备。但连长并没有责怪我们,也没有说重话。他先点评,后提了若干注意事项和基本要求,队伍就解散了回营房休息。从此我晚上睡觉再也不敢乱放衣服鞋子了。后来又搞了一次紧急集合,虽然仍然手忙脚乱,但起码没有出丑了。
新兵连是个全新的环境,与在城市里啥都依赖大人的学生生活,和为所欲为的农村当知青时最显著的变化,便是部队严格纪律的约束。我在新兵连听得最多的话,就是“从现在起不再是普通老百姓了,要拿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军人有啥标准呢?简单地说部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牢固建立“服从是军人的天职”的意识,有了责任担当。执行力也大为提高:做事要求风风火火,干净利落,行动讲究整齐划一。要堂堂正正,“动如风,坐如钟”。还要随时随地保持仪表尊严:着装要求衬衣扎在裤子里。再热的天,外出时军装的风纪扣必须扣好,军容必须整齐。出了营区,两人行走成横队、三人以上成纵队,行走必须抬头挺胸,不准勾肩搭背。说话要文明,不得口出狂言,不准大声喧哗;在营区内,着装要规范,不许光膀子,不能摇扇子,不让穿皮鞋,不得留长发。就餐要列队、唱歌,起床要叠被,熄灯后不准吹牛谈天等等,规矩多如牛毛。
要问为什么这样?大概军营是强健体魄铸造灵魂的地方,大家都能自觉自愿接受纪律的约束,把执行铁的纪律作为激发自尊心和进取心的保证。
一段时间的养成训练,体现出农村当知青与部队当兵的不同之处比比皆是:在农村知青韬光养晦、深藏不露。在部队军人铁血担当、光明磊落;在农村知青随波逐流、与世无争。在部队军人不怕困难、迎难而上;在农村知青拐弯抹角、欲言又止。在部队军人抬头挺胸、说到做到;在农村知青变通低调、八面玲珑。在部队军人争强好胜、团结合作;在农村知青查颜观色、世故圆滑,在部队军人令行禁止、坚决服从。我也感觉到这潜移默化的变化,发现新兵们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行事姿态都有了初步的改变,自由散漫的习气得到规范,作息时间也规律了,大家基本跟上了部队生活的节拍。
初来乍到的新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其中不乏志在千里,壮心不已的有为青年。新兵们来自大江南北,习惯迥然不同,特长各有千秋,能力半斤八两;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不本能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展示自己的风采。虽说也有个别崽儿求胜心切,表演过了头,闹过一些笑话,但追求上进的初心无可厚非。
五彩缤纷的新生活也开阔了我的眼界,学到了很多东西,收获很大。
在新兵连对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发生在到新兵连半个多月后的一次晚点名上。那天新兵连的指导员念了一张一个重庆新兵写的稿子,稿子不长,内容是表扬与他同班的一位广东农村来的新兵,每天早晨提前起床,为全班战士打好洗脸水,把大家的毛巾搭在脸盆的边缘,并将漱口杯的水灌满,把每个人的牙刷挤上牙膏,天天如此。指导员号召全连向广东兵学习,并话锋一转,又对写稿子的重庆新兵赞不绝口。说他不主动写稿子,这个榜样就可能埋没了。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广东新兵付出辛苦劳动,坚持天天为大家服务,的确不简单,值得表扬;而重庆新兵慧眼识珠,主动宣传战友的先进事迹,彰显了写作的价值,使两人都出了名,可谓一举两得获得双赢。这何尝不是更高明更巧妙的智力投资呢?
当然,能够提笔写稿,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这说明具备白纸黑字的写作能力,是一个很多人望尘莫及的优势。这种能力在当时部队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思考自己的发展选项,必须让思维发散,围绕自己的能力建立清晰的思路。须知人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资源有限,所以务必保持专注,不要试图同时做太多的事情。那何不把自己的写作特长转化为资源,并利用这种资源来打拼呢?
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把在农村当知青时记日记的习惯保持了下来。只是由于集体生活作息时间是固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有限,天天记日记有点吃力。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那是对圣人的要求。我等平凡人,平时有记的就记,争取星期天做个周记反省一下,或月底做个小结反省下自己就差不多了。
新兵连短短的那一个月训练,培养了我这个新兵军人的自觉与自律,体验了必要的程序感和仪式感。人生成功转型的巨大兴奋还没有消退,做什么事都自觉自愿,认真踏实,从不张扬,在集体中显得十分低调,表现得中规中矩,没有什么存在感,以至于有人说“看不出是个城市兵”。
不过这不是全部,其实我的心里也隐藏着有所建树的渴望。
有次安排全连新兵打扫环境卫生,任务是抜营区周围的荒草。我认为草扯光了风沙大,有点可惜。便一时搞忘了身份,还摆出当学生干部时的架势,振振有词地评头论足道:“留点绿色不好吗?”
不料被班长听到了,“喂,重庆兵,”他满脸不悦,十分恼火地出语训斥:“叫你干啥就干啥,哪来那么多废话。”
我其实不懂,这句话在部队里上级对下级说出来,并没有什么毛病。可我感觉班长的话里柔中带刚,既带着立场,更带有情绪,忍不住又竭力分辨:“我的好班长,拔了草地上光秃秃,遇到吹风泥沙随风到处飘散,其实弄整齐就行了。是不是嘛?”
旁边有个干部听到新兵蛋子居然“以下犯上”顶撞班长,大概觉得有点意思,戏谑道:“噫,这个重庆崽儿蛮有条理,似乎有点墨水,好好培养当个参谋应该没有问题。”
这当面夸奖一下子让我找不到北了,虚荣心强的老毛病说犯就犯。人人都知道:军队是个等级严密的组织,有发布命令与服从命令的一整套机制。天资愚钝的我,凭感觉认为“参谋”应该是个“官”,但不知道是个什么级别的官,还得意洋洋的在当天的日记里,正经八百的记下了《韩非子·显学》里的一句名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直到后来我下老连队之后,一次摆龙门阵时,无意之中听老兵说:“参谋不带长,打屁都不响”,我这才弄清楚,搞了半天参谋只是部队机关里从事军事业务工作的小干部,离“相”“将”相差甚远。要说那时的年轻人傻乎乎的,类似的糗事如今看来无疑是个笑柄,真是让人苦笑不已。但当时的思想就是如此的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