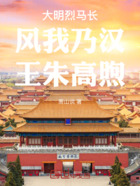
第47章 朱高煦满脸委屈
朱高煦那一番激情澎湃、滔滔不绝的怒喷,终究成功地让建文改变了心意。然而,倘若我们深入且冷静地去剖析,便会清晰地察觉到,朱高煦的言辞其实根本就缺乏坚实的依据,他所说的那些话语,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蛮横无理、毫无道理可言的道德绑架罢了。
徐滨指挥着聂兴等众多靖难遗孤,一次又一次精心谋划并付诸实践刺王杀驾的行动,可这一系列的举动,全然未曾得到朱允炆的授意,甚至朱允炆对此毫不知情。那身处奴儿干都司的三万靖难遗孤,的确是因为建文帝的缘故而深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在那荒芜偏僻、贫瘠荒凉且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竭尽全力地苦苦挣扎以求生存。然而,若是我们更为严谨地去探讨,造成这等凄惨绝伦、令人痛心疾首局面的始作俑者,绝非仅仅只有建文帝朱允炆一人,永乐帝朱棣同样有着难以推脱、无法规避的重大责任。
遥想往昔岁月,朱棣与朱允炆这对叔侄展开了一场激烈无比、惊心动魄的权力争斗。朱棣最终成功登顶,荣登皇位;而朱允炆则黯然落败,不仅痛失了大好的锦绣江山,更是失去了无数百姓的拥护与爱戴。就在此时,朱高煦站在那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上,蛮横地将靖难遗孤所承受的种种苦痛与磨难,一股脑儿地全部归咎于建文。面对如此这般的情形,朱允炆又能作何回应呢?难道在聆听了这些凌厉尖锐、毫不留情的话语之后,他还能够心如止水、毫无波澜,依旧安然地躲在庙宇之中,心无旁骛地参禅礼佛吗?显然,除了老老实实地选择回京,他别无他路。
朱高煦微微展露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与朱棣默契地交换了一个心领神会、饱含深意的眼神。朱棣,这位名垂青史、威名远扬的永乐大帝,其气魄之恢宏、胸怀之广阔,远远超越了常人所能想象的范畴。然而,一旦触及到皇权这一至关重要、不容有失的核心问题,他的心眼儿却比任何人都要狭隘!毕竟当年双方展开的那一场你死我活、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其过程之惨烈、斗争之残酷,其间所积累的种种恩恩怨怨、情仇纠葛,又怎么可能如此轻而易举、顺顺利利地就随风消逝、化为乌有呢?
朱棣一心渴望能够与建文达成和解,然而这和解必须严格依照他所设定的方式来推进。建文必须乖乖地回京,永远处于他那严密且全方位的监视之下。在这广袤无垠、辽阔无边的人世间,能够被永乐大帝深深忌惮、时刻防备的人物可谓是寥寥无几。其一,便是眼前这位身份极为特殊的朱允炆,毕竟他曾经稳坐皇位,威风凛凛地君临天下。其二,则是此刻隐匿于鸡鸣寺中、对世事不闻不问的黑衣宰相姚广孝。这位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背后的总策划师,其智谋之高深莫测,仿若妖邪一般神秘诡异,堪称是乱世之中的妖僧,同样为朱棣所猜忌和防备。
正因为如此,姚广孝极为明智、清醒地拒绝了高官厚禄,仅仅顶着些许徒有虚名、有名无实的虚衔,规规矩矩、本本分分地生活在朱棣的眼皮子底下,这无疑是一种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明智抉择。而朱允炆一旦决定回京,不管是选择潜心钻研、专注于参禅礼佛,还是牵头负责主持靖难遗孤的南迁返乡等一系列纷繁复杂的善后事宜,唯有如此,朱棣才能够真正地放下心头的顾虑、消除内心的担忧。故而,朱高煦当下所肩负的关键任务,便是绞尽脑汁成功说服朱允炆,令其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地回京,老老实实地待在那里。
所幸的是,朱允炆到底还是朱允炆,他那宽厚仁慈、善良温和的性情,向来为世人所称颂、所赞扬,绝非是徒有其名、浪得虚名之辈。最终,他还是点头应允了回京的要求,不过是以一介普通僧人的身份,而非太上皇那高高在上、尊贵无比的尊位。建文帝朱允炆,向来以宽厚仁爱、心怀天下百姓的美名而闻名于世,只是在对待自己的亲叔叔朱棣之时,他罕见地展现出了难得的坚决果断、狠辣无情的一面。
眼看着朱允炆点头表示同意,朱棣那颗始终高高悬起、忐忑不安的心,总算是稳稳当当、踏踏实实地落回了胸膛之中。紧接着,他迅速将目光转向了孙若薇,带着几分戏谑调侃的意味说道:“丫头,那你呢?”
孙若薇听到这话,瞬间呆若木鸡,整个人都愣住了,双眼之中瞬间盈满了迷茫与不知所措。她自小就被人反反复复地教导,必须要亲手斩杀狗皇帝,为自己的父母报仇雪恨,同时还要想方设法让那些靖难遗孤能够平安顺利地返乡。她的这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复仇这一坚定的目标而生,为了那些靖难遗孤能够过上安稳平静的日子而活。然而,历经了此前那一连串纷繁复杂、曲折离奇的风风雨雨,孙若薇早就已经清晰明了地认识到,倘若自己执意复仇,那些靖难遗孤必然会陷入万劫不复、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
于是,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放下那深埋心底、刻骨铭心的血海深仇,不辞辛劳、任劳任怨地为两位皇帝传递消息,满心期盼、全心全意地希望他们能够摒弃前嫌、冰释前怨,从而为奴儿干都司的兄弟姐妹成功求得赦免。但如今,两位皇帝当真达成了和解,奴儿干都司的靖难遗孤也确实如愿获得了赦免,然而她自己往后的人生道路又究竟在何方?一旦走出这座庄严肃穆、神秘莫测的灵山佛塔,她到底应该何去何从?
朱允炆瞧见她那满脸迷茫、困惑不解的模样,不禁微微一笑,语气温和地问道:“孩子,当你走出此地之后,可有什么具体明确、深思熟虑的打算?”
孙若薇先是迷茫地摇了摇头,紧接着又轻轻地点了点头。“大师,我想要协助您,主持靖难遗孤的南迁返乡这件关乎众多人生死存亡的大事。”
朱允炆微笑着点了点头,朱高煦却是在瞬间急得双眼通红,犹如两颗燃烧的火球。“丫头,他不过是个和尚,你跟着他能有什么作为?难道你是打算削发为尼,从此与青灯古佛相伴一生吗?”
“那我那可怜的壑儿,岂不是要伴着青灯古佛,孤独寂寞地终老此生了?”
此语一出,众人顿时哄堂大笑起来,那笑声在空气中回荡,犹如一阵狂风骤雨。孙若薇则是羞得满脸通红,那红扑扑的脸蛋仿佛熟透的苹果,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永远不再出来。
当此诸多事务都已尘埃落定,朱棣与朱允炆携手并肩一同走出了佛塔。行至塔外,只见徐滨等人双手被反绑着,整整齐齐地跪在地上。他们的身躯微微颤抖,眼神中透露出无奈与绝望。而朱瞻基与朱瞻壑这对兄弟,正悠然自得、怡然惬意地坐在一旁喝着茶水,那副闲适轻松的模样,与徐滨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直把徐滨等人气得咬牙切齿、怒目圆睁。
原来,就在朱高煦苦口婆心、费尽唇舌地劝说建文之时,赵王朱高燧已然率领着众多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锦衣卫高手,如疾风骤雨般对徐滨等人的据点发起了迅猛如雷、势如破竹的突袭。面对数十倍于己方的锦衣卫精锐,徐滨悲愤交加、义愤填膺,一心想要拼死决战、玉石俱焚。他的双眼燃烧着怒火,仿佛要将眼前的敌人全部吞噬。然而,就在他即将拔剑而起的关键时刻,却被朱瞻壑及时阻拦,并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建文绝对不会遭遇任何的闪失。正是因为朱瞻壑的这番保证,才勉强避免了一场惨烈血腥、两败俱伤的厮杀。
不过,还有一人的境遇格外凄惨,被里三层外三层地裹成了一个严严实实的粽子,几乎无法动弹。此人正是企图暗中行刺朱棣的聂兴。他的脸上充满了愤怒与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朱允炆目睹此景,当即扭头看向朱棣。朱棣此刻心情极为舒畅愉悦,宛如拨开云雾见青天。他懒得与这些人过多地计较纠缠,随意地挥了挥手,那手势仿佛在说:“罢了,都放了吧。”示意朱高燧将他们通通释放。
朱允炆望向徐滨等人,双手合十,轻轻叹息一声说道:“诸位施主,皇帝已然应诺,赦免所有靖难遗孤。贫僧亦决意回京,遁入空门。还望诸位施主能够放下过往的仇恨,开启全新的生活。”
话音刚落,朱允炆与朱棣旋即登上马车,车轮滚滚,扬尘而去,只留下徐滨等人呆立原地,面面相觑,满脸的茫然失措、不知所以。
所有的靖难遗孤都已经获得了赦免,这本应是一件值得欢欣鼓舞、普天同庆的喜事。然而,徐滨、聂兴等人的脸上却不见丝毫的喜悦之色,反倒是满心的怅然若失、忧愁苦闷。他们的内心仿佛被挖空了一块,空落落的,全然不知往后的日子应该如何度过。所有的麻烦事儿都已经解决完毕,可他们如今究竟应该走向何方?未来的道路充满了迷茫与未知,如同一片迷雾笼罩的森林,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朱高煦见此情形,笑眯眯地踱步走上前来,那步伐轻盈却又带着几分急切。他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这些人,目光中透露出一丝审视与盘算。“啧啧啧,瞧瞧这一个个身强体壮、肌肉发达的,可都是不可多得、极为难得的好劳力啊!”
“徐滨,聂兴,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跟着本王干一番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众人听闻,皆是一愣,脸上写满了惊讶与难以置信。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疑惑与警惕,仿佛在揣测着朱高煦的真实意图。
这汉王朱高煦,胆子也忒大了些!皇帝前脚才刚刚赦免了他们的反贼身份,您后脚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招揽?咋的?就这么急不可耐地想要让天下人都知晓您朱高煦心怀不轨吗?
赵王朱高燧也是惊得目瞪口呆、瞠目结舌,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嘴巴微张,半天合不拢。他压根儿就摸不透自家二哥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啥药,心中充满了困惑与不解。
“诸位放心,本王与你们素有交情,实在不忍心看着你们就这样虚度光阴、蹉跎岁月。”朱高煦试图安抚众人的情绪,让他们放下心中的顾虑。
“再者说了,就算本王有心造反,也断断不敢依靠你们啊!毕竟你们可是一群屡战屡败的造反失败者,不折不扣的废物……”朱高煦的话语中带着一丝轻蔑与不屑。
徐滨的脸上写满了愤怒与不解,心中的怒火瞬间如火山喷发一般熊熊燃烧起来。
你大爷的!你骂谁是废物?
“成与不成,给句痛快话,别在这儿磨磨蹭蹭、拖拖拉拉的。”朱高煦已然失去了耐心,满脸不耐烦、焦躁不安地催促道。
徐滨此人,倒也算得上是个人才,他平素所学皆是治国理政的方略之道,若就这样轻易放走,着实有些可惜。至于聂兴这帮子二五仔,权当是些添头罢了,留着充当下手马仔也还算不错。
徐滨原本想要一口回绝,但聂兴却在一旁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袖。顺着聂兴的目光看去,徐滨只见朱瞻壑正与孙若薇眉来眼去、打情骂俏,心中的怒火瞬间变得更加旺盛,当即改变了主意。
“好,我们愿意跟着您,干一票大的!”
朱瞻基默默地将这一幕尽收眼底,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忧虑与警惕。转身便急匆匆地跑去给朱棣打了个小报告。
朱棣听闻此事,心中不禁泛起了嘀咕,眉头微微皱起,陷入了沉思。赶忙将自家老二给召唤了过来。
朱高煦快马加鞭地赶到近前,还未站稳脚跟,便看到朱棣脸上挂着一抹似笑非笑、意味深长的神情,心中不禁“咯噔”一下。
朱棣缓缓开口问道:“你把徐滨等人给收编了?是不是有点儿操之过急、过于莽撞了?”
“爹,这些人所学的皆是刺杀之术,就这么放任他们离去,对咱大明而言,始终是个潜在的巨大隐患,倒不如将他们置于咱们的眼皮子底下,也好方便监管控制。”朱高煦赶忙解释道,额头上不知不觉已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朱棣听后,微微点了点头,若有所思。接着脸上泛起一丝笑意,那笑意却不达眼底,让人难以捉摸他的真实想法。他试探着问道:“你这回可是立下了大功,想要些什么赏赐?”
朱高煦心中一喜,以为机会来了,壮着胆子说道:“爹啊,要不您恩准儿子前往云南就藩?”
“嗯?怪不得你这会儿就急着收了这些刺客,原来是盘算着去云南招兵买马,造老子的反啊!”朱棣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眼神中透露出一股威严与愤怒。
朱高煦瞪大了双眼,满脸的委屈与无奈。
我嘞个去!
我这心态彻底崩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