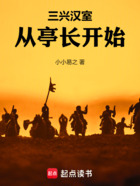
第54章 名额
听到部郡国从事史这几个字,刘珩再无疑虑。
心里既感叹杨毅思虑之周密,亦震惊于弘农杨氏势力之根深蒂固。果然真正的豪族,其核心力量永远隐没在水面之下。
说起部郡国从事史,就不得不提本朝的监察制度。
别看如今吏治混乱黑暗,但实际上,大汉朝的监察体系其实非常完善。
朝堂上,有御史台——凡天下诸谳疑事,掌以法律当其是非。掌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
御史台主官为御史中丞,秩俸千石,也是典型的位卑权重——这是本朝“三独坐”之一,地位尊崇(朝会上一般官员都是接席而坐,唯有尚书令、司隶校尉和御史中丞各自拥有专席,故称“三独坐”)。
地方上,监察系统则更加庞大。
县之游徼,便有监察乡里的职责。
郡国之五部督邮,分部循行属县,督察吏治。就是安喜县尉刘备前往拜见却见不到、因而强捆鞭打泄愤的那个督邮。
司隶校尉及各州刺史之部郡国从事,主督促所属郡国文书,察举非法,其实就是督邮的升级加强版。
而且这些人手下是有属吏的,权利范围极大,堪称除了州刺史以外,地方主官最忌惮之人。
程氏盐场触犯朝廷律法之事,基本是可以肯定的,并且十数年来所侵吞的盐税,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有负责河东郡的部郡国从事主导、背书,只要证据确凿、办成死案,程氏的确很难再有翻身的机会,除非幸存者借着黄巾起义的浪潮死灰复燃。
至于程氏背后势力的反扑......三世三公,跟你闹着玩呢?
从大义的角度上看,无论怎么说,杨毅督办此事都算的上为国尽忠。即使有些人不待见,明面上也得称赞一声“循吏”,想要报复,只能使用见不得光的阴暗手段。
但这些手段,杨毅不怕,刘珩也不怕。
畏畏缩缩,什么事都干不成。
“杨君两次屈尊下见,若刘某继续迟疑不定,未免也太不识好歹了。在下愿附于尾骥,辅佐杨君为国家剪除奸贼!”
“好!”
杨毅抚掌大笑。
......
虽然双方都已相互承诺,但杨毅显然不能立刻把盐官丞的印信交给刘珩,他需要完成一些必要程序,而且刘珩身上还有一个亭长的职位呢。
不过,区区亭长这种微末小吏,去职过程极为简单。
四月初时,便有县中官吏来到界亭,从刘珩手中收回安邑县县寺颁发的木制符传(刻有姓名、职务及管辖范围,作为执法凭据),查验归还的兵甲,封存库房——新任的界亭亭长还没确定下来呢。
而刘珩,则正式去职。
四月的最后一天,正值芒种,蚩尤里的农事基本告一段落。
杨毅再次登门。
不过这一次,就是非常正式的拜访了。
刘珩恭敬行礼,接过刻有“盐官丞印”四个大字的铜质方形印信后,便正式成为了河东盐官令下属的盐官丞,秩俸百石。
大汉朝明文规定,秩俸百石,月十六斛,半钱半谷。
意思是,百石官吏每月有十六斛(斛hu,和石一样都是容量单位,1斛=1石≈后世27公斤)粮食作为俸禄,但只给一半、也就是八石谷物,剩下一半折算成钱。
然而,让刘珩没有想到的是,杨毅送完印信后,不知是出于好意想帮助刘珩增长名望,还是别有用心,居然当众将委托刘珩招募属吏的事情说了出来。
这下蚩尤里瞬间变得热闹起来。
稍有些地位的官宦子弟,自然看不上盐官丞手下的这些小小吏员——除了两名佐史月奉八斛外,其余人的月俸只有四斛,大汉朝再没有比这更低的官吏了。
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吏员的位置不值钱,相反,任何时候,普通百姓对于皇粮的态度永远是趋之若鹜。
之所以如此,每月的四斛月俸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身份变化所附带的地位上的提升。
小吏再小,也是吏,身上也会有一层官皮。
然而,如此一来,刘珩在选人上却有些犯难了。
先不说里聚内的其他人,刘氏三个旁支的主事者——刘昱、刘朗、刘钧,连着几天,每天都要到坞院拜访一次,找不到刘珩就找刘珩祖母。
没错,就连一向跟主脉关系紧张的刘钧,也按捺不住,带着礼物上门,承诺以后完全听从主脉的调遣,绝无二话。
不过,刘珩心里始终没忘记此人曾陪同范鸿一起替赵谦纳妾之事。
范鸿这个谋害前身的凶手,已经在刘珩的必杀名单上。他死在黄巾动乱中,也就算了,万一侥幸活了下来,刘珩也会找“黄巾”处理他。
刘钧虽然没有大罪,可刘珩就是有些厌恶此人。
而刘昱和刘朗的请求,显然就不能忽略了。
一来,此二人帮过刘珩很多次,刘朗现在还在帮助刘珩收购粮食,恩情不能不还。
二来,在这个时代的普世价值观中,同族之人,是除了家人之外最亲近的、最值得信任的,而且汉人讲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更重要的是,刘珩也有将三个旁支纳为己用的想法。
所以他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分出一些名额。
这一日傍晚,刘珩正在里门附近来回踱步,刘预和周礼则跟在后面。
这二人是他选定的佐史。
周礼就不说了,他一定要留在身边的。刘预在他辞去亭长一职后,也跟着辞去了亭佐的职位。
二人分工稍有不同,周礼负责武事,刘预则偏文吏一些,主要是替他处理文书。
“这样吧阿预,除了你之外,我再给朗叔祖三个名额,昱叔祖那边同样也是三个,钧叔祖则只给两个。然后再从其他子弟中挑出两人,总共分出去十个名额。”
刘珩停下脚步,“但有一点,所需之人全部由你二人亲自挑选决定。身手、心性都好的,自然是最优选,若二者不能兼得,以性格为先。”
三分之二的老人加上三分之一的新人,应当算是相对合适的配比。
见二人应诺,刘珩微微颔首:“你们有两天时间挑选,两日之后,随我一起去解城上任。”
他嘱咐完,刚准备返回坞院,却见路上有一道身影正有些摇晃的走向里聚。
刘珩定眼一看,发现来人竟然是曾经找他借过钱的匡勋。
旁边的周礼面露嫌弃:“此人怕不是又去与人博戏了,这么晚才回来!”
刘珩看的更清楚一些,发现好像并非如同周礼所说的那样,匡勋之所以走路不稳,更像是劳累过度所致。
后者精神的确非常萎靡,走到近前,才看到刘珩三人。
“少君,竟这般巧合吗?”
他疲惫地冲刘珩行了一礼,从怀里取出一些铜钱,双手奉送给刘珩,“我曾找少君借过五百钱,今日还给少君。”
说完之后,整个人竟有一股如释重负的感觉。
刘珩眉头一挑,接到手里:“你家中的钱财,不都用来给祖父祖母治病了么,这些钱哪儿来的?千万别告诉我,是与人博戏赢回来的。”
“不不不。”
匡勋连连摇头,“我已经很久不玩博戏了。少君放心,这些钱是我在盐场做工得来的,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周礼见此情形,不由有些愧然。
只能说,人心中的成见,当真如同一座大山。
“你家中的田地,全靠你一人拾掇,竟然还有力气给人做工?”
匡勋笑了笑,没有说话,显得有些憨厚。
刘珩摇了摇头,将钱重新还给对方:“听说你准备迎娶寡嫂,这些钱,就当我送出的贺礼吧。”
他确实对此人有很大改观。
心中一动,问道:“愿意到我手下做个小吏吗?”
匡勋愣在当场,完全没想到这种好事竟然会落到自己头上,闻言连连点头不止。
......
五月中旬,刘珩带着三十名属吏一齐前往解城,正式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