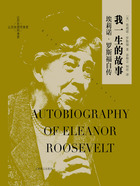
第一卷
我的故事
第一章
童年记忆
我的母亲(1)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豪尔一生从未涉足生意,他的父母为他提供了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他在纽约市西37街11号有栋房子,又在哈德孙河上游距离蒂沃里5英里的地方建了一栋,那里是人称“老法官”的利文斯顿(2)的地产。我外祖母的母亲是利文斯顿家的小姐,所以我们家和利文斯顿家族、克拉克森家族以及德佩斯特家族都沾亲带故,哈德孙河路上上下下各式各样的宅邸都是他们的房产。
我的外祖父豪尔最大的兴趣是研究神学,他的藏书大多与宗教有关。我还是个孩子,所以这些书都无法吸引我,但我却花了很多时间读多雷写的那本《多雷圣经画廊》,让我晚上可没少做噩梦!
我的外祖母豪尔夫人本姓拉德洛,她长得非常漂亮,大家都当她是家里的掌上明珠,还像小孩一样宠着她。她嫁给我的外祖父就是为了生儿育女,她一共生了七个孩子,但是她不用操心如何将他们抚养长大。外祖父从不对她说生意上的事,甚至连怎么写支票也没教给她。因此,当外祖父连遗言都没留就离世之后,抚养六个未满十七岁孩子的重任都落到了她的肩上,这是她完全始料未及的。
年龄最大的两个孩子,我的母亲和蒂茜身上已经展现出她们父亲的教育理念。蒂茜的原名是伊丽莎白,她后来嫁给了斯坦利·莫蒂默。她们非常虔诚地信仰宗教,把心思全都放在外祖父认为适合女孩子做的事情上。他对她们要求严格。在乡下,她们每天都要在背上背根棍子,弯曲双肘夹住棍子的两端,在家和大路之间来回走路,以纠正她们的仪态举止。她们读什么、写什么、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些外祖父全都严格把关,他让她们始终坚持最高的行为准则。这样教育的结果就是塑造了她们坚强的性格,对事情有着明确的是非判断,让她们符合传统的审美模式,这也是摆在她们面前唯一适合淑女的教育模式。
忽然间,那只强壮的手不在了,家里的两个男孩和两个年龄小一些的女孩还都懵懂无知。一个平日里只被当作孩子宠着的女人,怎么可能突然间就担起管教孩子的重担呢?
听人说,在外祖父去世后的前几年,我母亲成了全家的精神支柱,但是她在十九岁的时候就嫁给了我的父亲。
纽约这个社会自视甚高,我的母亲属于这里。彼得·马里那老头经常举办单身派对,他的赞赏对很多年轻姑娘和小姐来说,代表着成功。他称我母亲为王后,拜倒在她的美貌和魅力之下,这对她来说很重要。
在那个社会中,你要对穷人友善,要有博爱之心,要协助医院,为需要帮助的人献出爱心。你只能接受特定的人发出的聚餐、跳舞一类的邀请,你就属于那个圈子。你认真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你和大家读着同样的书,你对好的文学作品了如指掌。总而言之,你符合传统的审美标准。
我的父亲埃利奥特·罗斯福英俊迷人,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很喜欢他。父亲的家世背景和成长经历与我母亲的全然不同。他天生身体羸弱,这一点可能他自己也一直很难接受。十五岁那年,因为生病,他从圣保罗中学休学,一年后去了得克萨斯。他和那里的边境要塞麦卡维特堡的军官们交朋友,和他们一起玩狩猎、侦察游戏,寻找印第安人。他喜欢这种生活,他其实是个天生的运动员、优秀的射手和骑手。我觉得这段经历一定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虽然疾病也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但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都要依靠那些内心力量的支撑。当他回到纽约的家时,明显变得健康、强壮多了。
我父亲还未满二十一岁,祖父就去世了。那个时候,他的哥哥西奥多(3)战胜了纠缠童年的哮喘,去哈佛大学读书,后来成为美国总统。而他得到宽容的母亲和两个疼爱他的姐姐的许可,在继承了自己那份遗产后就去环游世界了。他在印度逗留了很久,当时可没几个美国人会干这种事。
为了参加他妹妹科琳娜的婚礼,父亲结束了旅行。科琳娜嫁给了他的朋友道格拉斯·罗宾逊。随后他也娶了我的母亲安娜·豪尔,但婚后的日子却是有悲有喜。
他和我的母亲彼此爱慕,但总是爱得含蓄矜持。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各自的家庭背景大相径庭。我父亲的家庭很少关注社会,也很少关注诸如纽约街头的报童以及谢菲尔医生努力救治的跛子这类小人物。谢菲尔医生是当时最有名的骨科医生。
我父亲的母亲和他哥哥年轻的妻子爱丽丝·李相继去世了。爱丽丝只留下了年幼的小爱丽丝安慰悲伤的父亲,他还很年轻。我父亲也深受丧母之痛。不过很快,就在1884年的10月,我出生了。根据大家的描述,我当时一定浑身皱巴巴的,比所有小孩都要难看,但是对我的父亲来说,我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
我两岁时依然是个严肃、腼腆的小孩,我敢说,即使是跳舞的时候我也从来不笑。我现在能记得的最早的事情,就是在一番盛装打扮之后,去给一群绅士们跳舞。当我在他们面前跳起芭蕾时,他们会鼓掌大笑。最后,我的父亲会把我抱起来高举在空中。他活着的时候影响着我的生活,即使去世多年以后,依然是我生命中爱的源泉。
和父亲在一起我真的开心极了。家里还留着那幅木版画,画上一个留着齐刘海的小女孩一脸严肃,抬着一根手指,满脸告诫的神情。父亲很喜欢这幅画,还取名为《小内尔在训诫埃利奥特》。我们在长岛的亨普斯特德镇上有一幢乡间别墅,父亲可以在那里打猎、玩马球。他很喜欢小狗和马,所以我们总是两种都养。在那段日子里,除了工作和运动,他还打理着自己的生意,一家人过着忙碌而快乐的生活。他不仅是我的全部世界,周围的人也都很喜欢他。
或许是因为他早些年生活压力太大导致身体虚弱,现在进一步加重了,也或许是因为他摔断腿以后反复接骨所带来的伤痛,我真的不知道什么缘故。父亲开始酗酒,而我的母亲、伯伯西奥多和姑姑们也开始替他感到忧心,直到1894年父亲去世。
1890年的冬天,为了父亲的健康、为了能够戒酒,父母带着我和弟弟去了意大利。我记得父亲扮成船夫的模样,带着我去了威尼斯的运河,还和其他船夫一起唱歌,我真的非常开心。我喜欢他的嗓音,更喜欢他宠着我。狄更斯的《老古玩店》里有个小女孩叫小内尔,父亲看过以后,就一直叫我“小内尔”。我在父亲心中是最重要的,这一点我从未怀疑。
然而,他也会被我惹恼,尤其是当我缺少勇气的时候,他会大失所望。但是很不幸,我常常让他失望。我们去索伦托的时候,有人给了我一头驴,让我可以骑着走过那些美丽的道路。一天,大家邀请我一起出去,但是在过第一个陡坡的时候他们就摔倒了,吓得我脸色苍白,宁可在大路上待着。我依然记得父亲那失望的语调,那些话语在我心中回荡了很久。
我记得和父亲一起去过维苏威火山,我们还往里面扔了硬币,最后拿回到手上的时候,硬币都裹上了熔岩,在那之后还有着漫漫的旅途。我猜想途中应该遇到了很多问题,我现在唯一能记得的就是感觉非常疲惫,还要强忍着不能掉眼泪,不然父亲会生气。
我母亲在临近巴黎郊区的纳伊找了所房子安顿下来,我们在那儿住了好几个月,因为6月底母亲就要生产了。父亲去了疗养院,他的姐姐安娜,也就是我们叫“拜伊”的姑妈陪着母亲。他们决定把我送去女修道院学习法语,防止孩子出生时,我在一旁添乱。
女修道院的经历可不怎么愉快。我当时还未满六岁,我一定非常敏感,因为我总是想得到别人的喜爱和表扬,这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长相平平又缺乏教养。我知道母亲因为我长得不好看而感到困扰,小孩子总是可以觉察到这些事。虽然她努力想把我抚养好,希望我很有家教,以此来弥补我相貌的不足,但是她的努力却让我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缺点。
修道院里和我同龄的孩子们,都对我这个既不会讲她们的语言,也不信仰她们宗教的女生没多大兴趣。她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神龛,总是花心思把它装扮的非常好看。我很想加入她们,但总是被排除在外,我只能一个人在四周都是围墙的花园里闲逛。
最终,我成了诱惑的牺牲品。有个女孩吞了硬币,所有人都对她格外关注,她成了大家的兴趣中心。我也想像她一样吸引每个人的注意。一天我跑到一个姐妹那里,跟她说我吞了一枚硬币。显然我的伎俩一眼就被看穿了,她们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很丢脸地把我带了回来。我现在能够理解母亲当时的感受了,因为我也成了母亲,有一个会撒谎的孩子对一个母亲来说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我记得坐车回家的途中真是苦不堪言,比起无休止的责备,我更愿意被揍一顿。只要能不挨骂,我就会撒谎,但如果知道惩罚也不过是上床睡觉或者打屁股这种,我可能也会说出真相。
撒谎的习惯陪了我很多年。母亲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小孩会因为害怕而说谎。我也是到了没什么可以感到害怕的年纪才改掉这个习惯。孩子出生后,父亲回家了,虽然我很遗憾他让大家都替他操心,但他是唯一没把我当罪犯看的人!
我弟弟豪尔才几周大的时候我们就乘船回家了,留父亲一个人在法国的疗养院。西奥多伯伯后来不得不去法国把他接回来。
那个冬天,没有父亲的陪伴。我在母亲的房间里睡觉,母亲晚上出门前都会打扮自己,我还记得我看到以后那种满心激动的感觉。她是那么好看,不管裙子还是珠宝,任何属于她的东西,只要能让我摸一下,我都开心得不得了。
那些年的夏天,父亲都在其他地方调养身体,所以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和外祖母一起待在她在蒂沃里的房子里。这里后来成了我和弟弟豪尔的家。
父亲把他的马送给了我们一匹,是母亲过去经常骑的那匹“老猎人”,我记得我也和母亲一起骑过。还有一件事我记得更清楚,就是经常去拜访姨奶奶拉德洛夫人,她的房子就在我们的旁边,但是更靠近哈德孙河。因为那一片的房子都离得很远,相互之间几乎看不到。
拉德洛夫人非常干练自信,是操持家务的一把好手。我记得有一次,她开始检查我的功课。可是我什么都不会读!从第二天开始,一整个夏天,她都让她的女伴玛德琳给我上阅读课。接着她又发现还有针线活、做饭,凡是女孩儿该会的我都不会。我觉得自己才只有六岁啊。
我猜母亲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因为从那以后,玛德琳就常常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开始教我做针线活。
我还和母亲一起睡,每天早上我都要向她背诵之前学过的《圣经·旧约》或是《圣经·新约》里的诗篇。真希望我现在还能记得那个夏天用心学过的所有东西。
有时我醒来,看到母亲和她的姐妹们还没睡,还在聊天。虽然很多都和我无关,但我还是怀着极大的兴趣一直在听。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懵懵懂懂的感觉,自己身边好像都是些麻烦事。父亲好像做错了什么,但在我心中,父亲是不会犯错的。
如果大人们意识到自己说的话在孩子内心掀起了怎样的波澜,我想他们应该会把事情解释清楚,但是没有人再对我说过什么。
在我七岁那年的秋天,我们搬回了纽约,房子是母亲之前买的,已经装修好了。我们住在东61街,和拜伊姑妈家只隔了两个街区。她住在麦德逊大道和东62街那里。泰迪伯父的女儿小爱丽丝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在抚养,那个冬天我们第一次真正熟悉起来。
她看起来长大了不少,还比以前聪明了,我很喜欢她,但是又有点儿怕她,即便是在我们都长大了,她成为白宫的“爱丽丝公主”之后依然如此。
那个冬天,我们和罗伯特·芒罗-弗格森成了朋友,这个年轻人被他哥哥从英格兰送到这个新世界闯荡。我父母认识他的哥哥罗纳德(后来被封为诺瓦尔勋爵),拜伊姑妈也认识。他被带进拜伊姑妈家,安排在道格拉斯·罗宾逊(4)的办公室做事,后来他成了全家人的挚友。
母亲总会在午后找点时间和我们三个待在一起。二弟埃利很喜欢母亲,真羡慕他从来不会挨骂。小弟弟豪尔总是被叫做“乔西”,他太小了,除了安心坐在母亲腿上,什么都不会。很奇怪,我感觉自己和他们三个之间被什么东西隔开了。母亲带孩子很努力,她会先读一遍,再让我读给她听;她会让我背诗;她会先哄弟弟们睡觉后再哄我上床。我现在依然记得,自己站在弟弟们的房间门口,把手指放进嘴里。我能看到她眼中的神情,听到她的声音,她说:“奶奶,进来吧。”如果有客人在,她会朝客人解释:“她是个有趣的孩子,很老派,所以我们经常叫她‘奶奶’”。我觉得很丢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忽然间,一切都变了!母亲得了白喉,那时还没有抗生素,我们三个被送到了其他地方。我去了教母亨利·帕里什夫人家,弟弟们送去了姨奶奶拉德洛夫人家,外祖母也离开家人前去照顾我的母亲。虽然立刻派人去通知了父亲,可是他远在弗吉尼亚,回来得太晚了。那段时间白喉非常猖獗。
我记得当时站在窗户旁边,苏茜表姐(帕里什夫人的女儿)突然告诉我说,母亲去世了。那天是1892年12月7日。我完全不懂得死亡意味着什么,有一件事扫除了一切阴霾。父亲回来了,我很快就能见到他了。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去世对他的打击到底有多大。他那些年带给母亲的悲伤如今全然被希望破灭代替。母亲把孩子留给了外祖母照顾。现在的父亲,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希望。
最终我们被安排和外祖母豪尔夫人一起生活。我现在才意识到,外祖母家一定被我们搞得乱七八糟。两个舅舅和两个阿姨还在家里住,他们的温柔体贴让我无比惊讶,因为他们的言行举止让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外人。
我们被安顿好以后,父亲来看我了,我记得我走进西37街一处房子一楼的书房。那里天花板很高,光线很暗,父亲坐在一张很大的椅子上。他穿着一身黑,看起来非常伤心。他伸出双臂把我抱到跟前。过了一会儿,父亲开始说话,他向我解释说母亲走了,她曾是他的全世界,如今他只有我和两个弟弟了,弟弟们还小,所以我和他必须相依为命。总有一天,我会再给他一个家,我们会一起旅游,一起做很多事,很多父亲觉得开心有趣的事,这些将来一定都会实现。
很奇怪,在我心里总是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把弟弟们当成我们的孩子,或是他觉得他们会去上学,然后变得独立。
从那天起,我就一直有种感觉,父亲会和我紧紧相依,总有一天,我们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他告诉我要经常给他写信,要做一个乖孩子,不要闯祸,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要成为他的骄傲,他一有时间就会回来看我。
父亲走后,我独自一人守着我们的秘密,努力适应新的生活。
两个弟弟和玛德琳睡在一起,我在他们房间外的走廊上支了张小床。我已经到了可以照顾自己的年纪,只是我的头发得在晚上梳好。当然,必须得有人接送我上下课,而且不管我下午做什么,都得有人跟着。我有家庭女教师、法国女仆和德国女仆。我会走得很快,把她们都甩掉,她们总想和我说话,我只希望自己一个人沉浸在梦里,在梦中我是女主角,父亲是男主角。只要我一上床或者早晨一睁眼,我就会回到梦里,我走路或者有人烦我的时候也是如此。
虽然我身体很好,但是一到冬天就时不时喉咙痛、扁桃体发炎,所以规定我每天早上都要洗冷水澡,我该如何逃过这些冷水澡!玛德琳不会总跟着我,所以没人监督的时候,我就往洗澡水里加更多的热水。
外祖母非常重视教育,所以我必须要学法语,父亲又希望我能懂音乐。我到十八岁才开始学习音乐,但是之前根本没有人训练过我的耳朵!一直到听了普茜阿姨弹琴,我才懂得体会音乐所传达的情感。普茜阿姨是那么可爱迷人,听她弹琴是我童年又一件难忘的开心事。
我或许有当歌手的潜质。我发现歌手总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当然更重要的是,会博得关注和喜爱!这是我童年梦寐以求的,因为我很清楚,在我身上没有什么可以吸引大家关注或喜爱的东西。
现在回过头来看37街那栋房子里的生活,我才发现那段在纽约的日子是多么与众不同,连房子和街道也是。那里有很多很气派很漂亮的房子,大多都在第五大道上。麦迪逊广场依然都是住宅区,第14街到第23街是商业区。
街上没有汽车,取而代之的是漂亮的马匹和灵便的马车。第五大道上主要是马拉的大车,马拉的小车则在其他大道以及横穿的街道上。出租马车和双轮双座马车就是当时的出租车。
我们那座老式的褐砂石房子和街上其他房子一样,非常气派舒适,有高高的天花板,阴暗的地下室,还有拥挤的仆人宿舍,那里既是他们的住处也是工作的地方,今天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人恐怕都无法忍受这样的条件。洗衣房有一扇小窗开向后院,当然我们没有电灯,只有瓦斯,那个年代有瓦斯就已经很先进了。
仆人们住的房间通风不畅,没有像样的家具。他们的厕所在地下室,所以在那间狭小的卧室里,每个人都有一个洗脸盆和一个储水的陶罐。
我们家有厨师、男管家、女仆和洗衣女工各一名,女仆还要同时侍奉我的小阿姨们。家里还有外祖母、普茜阿姨、莫德阿姨、瓦利舅舅和埃迪舅舅。莫德阿姨在我们来之前一直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瓦利是大舅舅,还有不经常在家的埃迪舅舅,应该比瓦利舅舅小两三岁。埃迪舅舅一直在到处旅游,在我的记忆中,他去过遥远的非洲。
我和两个弟弟以及他们的保姆住进了这栋房子。
虽然我现在觉得外祖母当年依然非常年轻,但是当时她在我眼中非常苍老。她几乎一直待在自己的卧室里,有客人拜访时,她才会下楼会客。用蓝色绸缎罩着镀金家具的客厅成了外祖母见客人的地方,因为书房被她的女儿们占用了。书房是一间很大的前厅,那里放着一架钢琴,临街一侧开有一扇大圆肚窗,这让房间的采光非常好。
房子后面新建了餐厅,侧面有三扇窗户,所以餐厅很亮堂。再后面是男管家维克托的储藏室,他对我很好,教我怎样洗盘子、擦盘子,虽然盘子摔碎时他会很不高兴,我在那块地方度过了很多时光。有时候我很不讨人喜欢,没吃晚饭就被送去睡觉,维克托或是女仆凯蒂就会偷偷给我带些吃的。
外祖母这些年改变了很多。她对自己的儿女倾注了满满的爱,但是管教孩子一直是外祖父的责任。外祖父去世后,外祖母依然扮演着慈母的角色,但是不久她便发现,四个孩子她一个都管不了。现在孙子也由她照顾着,所以她决定一定要严加管教,不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溺爱。拒绝要比答应更容易说出口,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家教下长大的。
回想起小时候,我总是害怕很多事:怕黑、怕惹别人生气、怕失败。我总要先克服内心的恐惧才能做成某件事。十三岁时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普茜阿姨生病了,喉咙痛,非常严重,她喜欢指使我替她做事,这让我觉得非常荣幸。有天晚上她叫我,四周漆黑一片,我只能摸索着去她房间。她问我能不能帮她去地下室从冰箱里取些冰块。这意味着我要走下三层台阶,而且在最后一层台阶那儿还要关上门,独自一个人待在地下室,在黑暗中找到放在后院的冰箱!
虽然我的双腿不停地打战,但是在不敢去和因为害怕而不能照顾生病的普茜之间,我别无选择。我拿回了冰块,这再一次证明,对小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向身边人证明自己有用更重要的了。
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周围的人总在经受这样那样的苦难。在我五六岁时,父亲曾带我去一家报童之家准备感恩节晚餐。伯父西奥多·罗斯福创办了很多报童之家,他还在“儿童援助协会”当了很多年董事。父亲跟我解释说,这些衣衫褴褛的小男孩们大都无家可归,只能住在空地上搭建的木棚里、别人家门前的走廊、公共建筑或其他能够栖身的地方,但是他们都很独立,能够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每年圣诞节,外祖母都会带我去帮研究生医院的儿童病房装扮圣诞树。她非常热衷这类慈善活动。
格雷西姨祖母则会带我们去整形医院。这家医院是由祖父提供医疗器材,帮助牛顿·谢弗医生创办的,祖父一家都对这家医院投入了很大精力。我在那里看到很多幼小的孩子身上都打着石膏或夹板,有些保持奇怪的姿势躺了好几个月。我对他们尤其感兴趣,因为我自己就有脊柱侧弯,有时候会穿钢制的支架,真的非常难受,还不能弯腰。
瓦利舅舅是一名网球冠军,在纽约很受欢迎,哪怕是过圣诞节他也要忙着比赛。不过即便如此,他也会带我去纽约城一个叫“地狱厨房”的地方,帮那里的孩子装扮圣诞树。这里多年来一直是纽约最贫穷困苦的地方。我还和莫德阿姨、普茜阿姨一起在包厘街救济所唱赞美诗。这些经历让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富足的生活和那些地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虽然父亲很少和我们待在一起,但是他却成了我这段时期生活的全部。我总是下意识地期盼着他的到来。虽然他来期不定,也很少事先捎口信,但是只要父亲一进门,即便我在房间里也能立马听出他的声音,我的房间和大门可是隔着两层长长的楼梯。走下楼实在是太慢了,我便顺着楼梯的护栏滑下去,通常父亲才刚摘掉帽子,我就已经扑到他怀里了。
父亲每次都会给我们带礼物,更别说圣诞节这样的大日子了。有一年的圣诞节至今仍历历在目,因为我收到了两只袜子,一只是外祖母送的,另一只是当时还在纽约的父亲在圣诞节那天早上带给我的。
母亲去世后的那个冬季,又发生了一件事让父亲心力交瘁。二弟埃利自从母亲走后一直病怏怏的,他和小弟弟乔西都得了猩红热,于是我被送到苏茜表姐家,当然,我也被隔离了。
乔西的病情稳定,身体逐渐好转,但是埃利却恶化成白喉,最终离世。父亲有时会过来带我出去,但是弟弟们的事情对他来说打击太大,以致他和我在一起时也总是忧心忡忡。
1894年8月14日,就在我十岁生日前夕,有消息传来说父亲去世了。虽然我的阿姨们也是这么告诉我的,但是我绝不相信,我哭了很久,睡觉的时候还在哭,最后哭着睡着了。然而第二天醒来又像往常一样活在我的幻想中。
外祖母决定不让我们这些孩子参加葬礼,因此死亡对我来说依然是虚无缥缈的。从那时开始,我心里明白,父亲死了,但是我心里和他更亲近了,可能比他在世时还要亲近。
我的父母都很喜欢让我们多去拜访格雷西姨祖母,她深受侄孙侄孙女们的喜爱。我现在仍记得,格雷西姨祖母虽然身高中等,身形纤瘦,但是看起来总是那么美丽优雅。当时女士们都穿那种上有束胸、下有圆摆的拖地连衣裙,但我依稀记得,格雷西姨祖母经常穿一件紧身胸衣,胸衣的背部是正常高度,胸前是方形领口,脖子周围还有白色的蕾丝或亚麻的褶边做装饰。
她给我们讲故事时,双手常常叠放在大腿上。虽然还是个小孩,但是我很喜欢观察人们的手,我记得看着格雷西姨祖母的手时,真是赏心悦目。我的周六经常和这位和善可亲的姨祖母一起度过。爱丽丝·罗斯福、泰迪·罗宾逊和我三个人最享受那段时光。
父亲去世后,我就不允许出门和格雷西姨祖母一起过周六了。外祖母觉得我们应该尽可能待在家里。罗斯福家的亲戚都很有活力,她可能担心我们和他们走得太近,会管不住我们。
接下来的几年对我来说平淡无奇。纽约进入冬季,我要去学校,还要去补习班,偶尔在周六下午,和一两个小伙伴一起吃晚饭、玩一会儿,就当是娱乐了。外祖母想要把我打扮成小孩子的模样,阿姨们却觉得我应该穿符合我年纪的衣服,但是又不合身。我高高瘦瘦,又很害羞。我去上舞蹈课或参加聚会的时候,她们给我穿长度在膝盖上面的小短裙,可是跟我同龄的女生大多穿长度到小腿肚的裙子。现在看来,当时我所有的衣服只会让我觉得尴尬局促。
从11月1日到次年4月1日,不论气温高低,我一直穿着法兰绒的衣服,从头盖到脚。当然,里面还穿了法兰绒衬裙和黑色长筒袜。这得多热啊!而且我还穿了系扣子或绑带子的长靴,因为这样可以让脚踝变瘦。
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都待在蒂沃里的房子里,只有一个保姆兼家庭教师陪着,其他人都不在。蒂沃里的夏天闷热难耐,我弹钢琴的时候手指都黏在了琴键上,即便如此,我也没有脱掉一件衣服。即使在夏天,我们这些孩子都会穿很多。我有时会把长筒袜往下褪,但是会被提醒说淑女绝不会露出她们的双腿,于是立马又把袜子穿好!
我们在蒂沃里的房子很大,有高高的天花板,还有很多大房间。外祖父把楼下装修的相当正统,放了很多好看的大理石壁炉和枝形吊灯。我们没有瓦斯和电,所以枝形吊灯是用来点蜡烛的。虽然我们有油灯,但还是经常借着烛光去睡觉。楼下还有玻璃橱窗,陈列着从世界各地收藏的珍宝,有不少精致的象牙微雕工艺品,一套微型桌椅,还有银饰品、小瓷瓶以及珐琅釉的物件,我很喜欢那套微型桌椅。
书房除了外祖父的宗教类书籍外,摆满了各类名著。很多小说是年轻的舅舅、阿姨们放进去的。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那么多狄更斯、司各特和萨克雷的书,被大家读了一遍又一遍,尤其是埃迪读得多。
二三层有九间主人卧室、四间仆人住的双人房和一间单间。仆人在这儿住的房间可比在市区的好多了,但是仆人没有浴室,而且没人会觉得这很奇怪。虽然在这座大房子里只有两个浴室,但是对我们来说并没有觉得使用不方便,或是在我们自己的房间用盆和陶罐洗会很麻烦。
小孩子每周必须洗两次热水澡,虽然我觉得外祖母可能仍然记得那只有每周六晚才能洗澡的年代。我每天早上还要用海绵沾冷水擦身体。
外祖母每天早早起来做家务的时候会让我跟着,我就把她从储藏室里仔细称好的面粉、糖和咖啡拿去给厨师。厨房是那种大大的老式厨房,外面有一圈大石头围成的天井,再上面就是院子,只有一小块地方可以让太阳照进来,如今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在这种光线半暗的厨房里做饭了。仆人们吃饭的地方有扇门通向天井。洗衣房稍微好点儿,因为有两扇门通往露天平台,我经常在那里玩。
我们那么多人的衣服都是欧沃豪斯太太一个人洗,既没有洗衣机,也没有电熨斗可以帮她。她有一根洗衣棒、三个桶、一台拧干机和一个烧煤或柴火的炉子,炉子上面是各种大小不一的铁块。
欧沃豪斯太太身体不错,是个乐天派,她生了很多孩子。显然她会先把自己家的家务安排妥当,然后来我们家洗洗涮涮一整天,晚上再回去接着干农场的活。她教我洗衣服、熨衣服,虽然她只允许我做一些简单的事,但是手帕、餐巾和毛巾经常交给我来洗。我很喜欢和欧沃豪斯太太待在一起,她总是很开心。
普茜阿姨的性情很像艺术家,有时候我会去找莫德阿姨一起玩,因为普茜阿姨不和任何人说话。渐渐地,我开始试着把它当作她性格的一部分,对她做出的所有可爱举动都心存感激,耐心等待暴风雨过去。
有一年夏天,她带我和我的女家庭教师一起去楠塔基特岛旅游,我们在那儿待了很多天,对一个只在哈德孙河附近玩耍、没有去过其他地方的小孩来说,这趟旅程真是令人无比激动。几天后,我感觉普茜阿姨应该是和我们在一起待腻了,总之她先离开了。虽说她还会回来,但是我觉得她已经把我们忘到了脑后。家庭教师身上的钱又不够我们俩回家的路费,最后还是求助外祖母寄钱帮我们付了账单才回的家。
当年轻的舅舅、阿姨们离家以后,我感到更加孤单了,但是这种孤独感也让我养成了习惯,我会带着书去田野里、树林里,或坐在树下、或躺在地上,全然忘记了时间的流逝。除了有时候遇到书中不懂的地方向其他人请教过后,那本书就会消失之外,没人会监视我在读什么书。我记得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就是这样消失的,我还找了好久。
外祖母在有些事情上有她自己的坚持。比如周日的时候我不能温习功课,我得去主日学校给马车夫的小女儿上课,教她读诗,听她背诵,看她学习赞美诗、短祷文和教义问答。这些我也都要学习,然后背给外祖母听。
每周日年龄大一点儿的维多利亚都会来家里找我,我们一起去教堂,我经常坐在外祖母对面那个小座位上。烦人的是,这4英里对我来说太长了,几乎每次还没走到教堂,我就觉得恶心想吐,回家的时候也是如此,还没到家就想吐。
我周日不能玩游戏,我们虽然中午还没做到不吃热食,但是晚上是不能吃的,这是外祖父的规矩。
玛德琳终于成功教会了我针线活。我开始给擦碗巾缝边,织补穿破的长袜。玛德琳可让我流了不少眼泪,因为我真的非常怕她。我曾经很喜欢在冰窖长满苔藓的屋顶上往下滑,结果我的白短裤被蹭成了绿色。我会在见玛德琳之前先去找外祖母,因为我知道外祖母不会过分责骂我。
虽然我不应该在早饭前躺在床上看书,但是夏天每天早上我几乎一到5点就醒了,我想我当时可能有点儿任性,我会在床垫下面偷藏一本书。可要是被玛德琳抓到我在看书那可就惨了!
我已经不记得为什么会那么怕她。虽然现在回头想想确实非常可笑,但是我好像直到十四岁,有一天和外祖母在树林里散步时,才告诉她我有多怕玛德琳,接着就是在抽泣声中向她一五一十地诉苦。现在想想真的好傻啊。
那段时间我有几件事就觉得非做不可。我记得十二岁的时候,亨利·斯隆先生叫我和他的女儿杰西一起去西部。我以前都没想到我此生会那么渴望去做某件事,因为我很喜欢杰西,又很想去旅游。但是外祖母态度很坚决,也没有跟我解释什么原因,就是不允许我去。她觉得自己的决定很明智,这很没有道理。外祖母经常把“不”挂在嘴边,于是为了提前防止她拒绝,也为了降低我的期待值,我会先说我不想做这些事。
外祖母觉得我应该学跳舞,所以我就去上了多兹沃斯老师的舞蹈班。这个机构成立了很多年,推出了各种不同的课程,很多小男孩小女孩在这里学习波尔卡和华尔兹,他们站在一块块擦得锃亮的菱形实木地板铺成的教室里,非常认真。
由于我日渐长高,可能看着还有点儿笨手笨脚,所以外祖母还让我去学芭蕾。因此我每周都要去百老汇大街上一节芭蕾课,和其他四五个女孩一起学习用脚尖跳舞。她们在一起谈论说都想当舞蹈演员,现在正在找机会进舞蹈队云云,这让我非常嫉妒。
我喜欢芭蕾,也刻苦练习,我明白什么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即便是舞台上看起来非常简单的动作,演员在台下也付出了不知多少努力。
(1) 安娜·豪尔·罗斯福(Anna Rebecca Hall Roosevelt,1863—1892),1883年12月1日与埃利奥特·布洛克·罗斯福(Elliott Bulloch Roosevelt,1860—1894)结婚,埃利奥特是后来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弟弟。婚后育有一女安娜·埃莉诺·罗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即本书作者;两个儿子:小埃利奥特·罗斯福(Elliott Bulloch Roosevelt,Jr.,1889—1893)、格雷西·豪尔·罗斯福(Gracie Hall Roosevelt,1891—1941)。——译者
(2) 罗伯特·R.利文斯顿(Robert Robert Livingston,1746—1813),是《独立宣言》五人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同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一同起草和签署了《独立宣言》,见证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译者
(3)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人称“老罗斯福”,昵称“泰迪”(Teddy),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堂侄富兰克林·罗斯福日后也当选为美国总统,人们常称其为“小罗斯福”。——译者
(4) 小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 Jr.,1855—1918),美国企业家,纽约市著名的房地产经纪人,娶了科琳娜·罗斯福(Corinne Roosevelt),即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妹妹,也就是本书作者埃莉诺·罗斯福的姑妈。——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