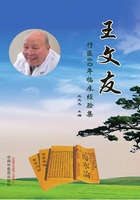
上篇 从医之路
师从名医兼容并蓄
我1934年出生于山东文登,幼时随父母迁至辽宁丹东,舞勺之年即入当地名医孙华山诊所学习,并经常跟随孙师到周边乡镇巡诊,对中医内、外、妇、儿等科的多种疾患都有所涉猎,目睹了不少疑难杂症,也了解和掌握了许多民间草药、单方、验方、偏方,以及针灸穴位和技法,特别是孙师在“接骨”方面的技艺。如广为流传的“激怒整复法”,就是对于一些因为骨折、脱臼或严重扭伤引起的疼痛而拒绝检查和治疗的患者,孙师会故意用语言激怒对方,然后出其不意,趁其不备,对准患处猛击一掌,便一蹴而就了。孙师告诉我,这就是利用中医的“七情为病”对应脏腑五行相克原理进行的辨证施治。孙师的绝技不单单是手法,他的内外用药,也是活人无数。孙师不仅身怀绝技,而且不乏爱国、爱民、爱党之心。当年,他赴日为中医骨伤争光,曾拒绝天皇的挽留,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他的诊所,一向主张“有钱没钱都看病”,他多次为贫困患者掏钱买药。正是这些所见所闻与亲身感受,坚定了我投身中医学事业的信念,把治病救人、扶危济困、成为“苍生大医”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在孙师指导下,我开始研习《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每日背诵,勤学不辍,并将临床所见与经典学习相结合,深入体会经典深意,为打下扎实的中医功底,学习从来不敢有一丝懈怠。
学习《内经》,我对脾胃的领会尤为深刻。脾与胃五行属土,以膜相连,经络连属,互为表里。《素问·厥论》以“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明确了脾胃相互的关系。《素问·灵兰秘典论》中“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素问·经脉别论》中“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阐明了胃主受纳腐熟,脾主运化升清,使饮食水谷化生为气血精微,转输营养周身的过程。《素问·玉机真脏论》中“脾为孤脏,中央土以灌四傍”“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说明了脾胃为气血之源,可充实营卫元气,滋养脏腑肌腠,使“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能提高预防疾病的能力。《灵枢·五癃津液别》言“脾为之卫”,指明了脾能提高人体的防御能力。《素问·刺禁论》又称:“脾为之使,胃为之市。”“使”“市”有畅通无阻之意,可引申为“转枢”,指明脾胃位居中焦,一主升清,一主降浊,是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内经》指出脾胃病的病因涉及“思伤脾”“饮食自倍”“用力过度”等方面,病机以“阳道实,阴道虚”为特点。诊法亦独重胃气,如《素问·脉要精微论》中“夫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指察五色以明润含蓄有胃气者为佳;《素问·平人气象论》中“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脾胃病的治则,《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土郁夺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主张“中满者,泻之于内”等。治法以针刺为主,亦有兰草汤、半夏秫米汤等方药。预防措施则主张饮食“食饮有节”“谨和五味”“寒温中适”。这些理论充分说明了脾胃作为后天之本的重要地位和在人体气的运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在以后的行医治病中我始终注重顾护脾胃这一主要观点,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病风格。
对肝之生理、病理特性的理解亦始于《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灵枢·本神》曰“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素问·灵兰秘典论》曰:“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其阐明了肝体阴用阳,性生发条达,主司疏泄的特点。对肝病的脉、症、诊法、病因病机和预后判断,《内经》也有诸多记载。《灵枢·五阅五使》之“肝病者,眦青”,《灵枢·师传》之“肝者主为将,使之候外,欲知坚固,视目小大”及《灵枢·五色》所述“下极者,心也;直下者,肝也”,皆是候肝望诊之法。《素问·平人气象论》曰:“平肝脉来,耎弱招招,如揭长竿末梢,曰肝平,春以胃气为本。病肝脉来,盈实而滑,如循长竿,曰肝病。死肝脉来,急益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素问·玉机真脏论》称:“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如按琴瑟弦”,形象地描绘了肝之平脉、病脉、死脉、真脏脉之特征。《灵枢·本脏》讨论了肝之大小、坚脆、高下对体质的影响。《灵枢·本神》记述了情志伤肝的机制和临床表现:“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则是对肝病病机的经典总结。在治疗方面,《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以“木郁达之”为治则,《素问·脏气法时论》用“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确定了用药原则。《灵枢·五味》中“肝病禁辛”“脾病禁酸”“肝色青,宜食甘,秔米饭、牛肉、葵、枣皆甘”,则从五行生克角度为肝病食疗提供了指导。在临证治病时,我时刻结合以上理论,逐渐悟到人体气机的畅达、水谷的运化、气血的化生、情志的调和、血液的收藏皆有赖于肝气,调畅肝气遂成为我治病的核心原则之一。
通过研究学习经典著作和开展愈加丰富的医疗实践,我深谙脏腑之性,尤其是脾为后天之本、胃为水谷之海及二者之间关系在临床疗效中重要地位。我认为,脾胃之升降互根乃是人体周身气机调畅的关键,故治脾当主以升清,治胃当主以降浊,以顺其性。在遵从《内经》理论的基础上,我又从五行生克的角度进一步探究脾土与肝木之间的相互作用———脾生化气血可养肝体,肝疏泄气机可行脾气,土能壅木,亦能荣木,木能克土,亦能疏土,肝脾二脏并治,常可事半功倍。特别是临床所见湿热合邪为病,我认为其根源亦多在于脾土,而湿土壅滞者尤需以风木疏之,更当以肝木脾土同治为法。
1953年,为了进一步深造,实现“苍生大医”的目标,我前往北京,进入伤寒大家陈慎吾创办的北京中医研究所(后更名汇通中医讲习所)进行系统学习。陈师在《伤寒杂病论》教学时,严格要求学生从原文入手,要将书中脉证方药了然于心,才能做到以不变应万变。5年的学习,在陈慎吾、于道济、穆伯涛、余无言、耿鉴庭、赵绍琴、谢海洲等老前辈的言传身教与面命耳提下,我习诵经典,侍诊左右,系统学习了《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中医经典,《中药学》《方剂学》《中医诊断学》《中国医学史》等中医基础课程,以及内、外、妇、儿、针灸等临床学科。此次的学习,对我以后的从医经历起了尤其重要的作用。
陈慎吾教授(1897—1972),师从唐宗海之弟子河南名医朱壶山,崇尚仲景学说,一生致力于《伤寒论》研究。主张《伤寒论》《金匮要略》本为一体,必须结合起来学习,重视条文间的连贯和前后对勘。提出《伤寒论》是辨证论治的专书,掌握其“法”需注重方证和相似症状的鉴别。诊病尤重腹诊、脉诊,强调“药不治病”“正气自疗”,人体本身的正气在发病和治疗中具有关键作用,以“阴阳调和”为痊愈之理。陈师在所著《伤寒论讲义》中称:“正气生于胃气,经之有胃气者生,即胃气能自疗其疾也。明于此则全篇大旨自得,阴阳寒热,虚实损益,无非保其胃气使之自疗。”认为《伤寒论》虽未直言“保胃气,存津液”,但细察用药、禁例、调护等诸多方面,这一精神已贯穿全篇。
1955年,在汇通中医讲习所学习的同时,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北京南城永定门外开设“王文友医寓”进行诊疗活动,学以致用,造福于民。通过独立应诊的经历,对经典的理解更进一步,积累了丰富的临证心得;日益丰富的见闻,使我进一步领会“事要知其所以然”。我继承了《伤寒论》和陈师重视人体正气,注重“保胃气,存津液”的学术观点,在辨证论治、遣方用药、养生调摄等方面都强调顾护脾胃。对《伤寒论》治肝诸法体会颇深,我认为肝虽秉风木之性,却为质柔之脏,需以阴血为养,故施以疏利攻伐时当谨慎为之,注意勿伤其阴,病变累及本脏形质者更要以柔养为主。在湿热证的治疗中,深得仲景“辛开苦降”用药之法的精髓,临床常灵活运用小柴胡汤类方、泻心汤类方等经典方剂加减施治,效如桴鼓。1957年,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医理论和临床技术水平,我和李广钧、马文慧、苗昕先后拜京城名老中医王友虞为师,成为王友虞的亲传弟子,深研《黄帝内经》《难经》,并侍诊左右。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下,我获益良多。
王友虞教授(1912—2005),新中国成立前在北平开设天寿堂医馆,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主任医师,老干部保健医。著有《太极保健秘旨》《中医妇科秘旨》等医籍。
1958年,我以优异的成绩从汇通中医讲习所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在宗维新、白啸山、马秉乾、周慕新、许公岩、方和谦等教授的教导下,更系统地学习了中医各科理论水平,同时增加了西医基础学科的学习,为今后的临证打下了更为扎实的基础。
1959年,我被分配至北京市中医医院内科工作,师从中医肝病专家关幼波,在名师关师的亲授下,多得所传,对以后疾病尤其是肝病的治疗影响深远
关幼波教授(1913—2005),多年专注于中医对肝病的研究,总结出“治肝十法”,提出按病因、病位、气血辨证黄疸,分清湿热偏重、在气在血,以“活血”“解毒”“化痰”三法治疗,创立“络病”“虚证”等诸多学说。关师在传统的“八纲辨证”基础上加入“气血辨证”,倡导“十纲辨证”,气血之中又以气为核心。他还注重“痰瘀学说”,认为病之所成,是由气及血,气滞则血瘀、痰生,痰瘀互结是慢性肝病难以治愈的根本原因,化痰活血的治则要贯彻始终。治痰、治瘀的法则,又以“治气”为先。人体阳气畅行,则邪不能害,肝胆秉春木之气,蕴正气生发之机。而“调理肝脾肾,中洲要当先”,治肝当先实脾,也是关师治疗肝病要诀之一。
在北京中医医院工作期间,通过对大量肝病患者的诊疗,我对肝脾两脏的联系和湿热之邪致病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肝与脾在人体水液代谢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脾主运化,肝主疏泄,水湿不化责之于脾,水道不利求之于肝。湿热之邪为患广泛,可弥漫表里上下,累及诸脏诸腑,治疗当祛邪为先,又重调理气机,需使升降出入之途径通畅,脏腑运化、疏泄之功得以恢复正常,才能从源头上治理水湿。
1962年,我赴北京市石景山防治院从事临床工作。1979年初,考入北京市中医师资进修班,由著名中医任应秋教授、赵绍琴教授、刘渡舟教授等授课任教。对经典著作《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学习了《医古文》《中医各家学说》《中医教学法》《医学心理学》《编写教学大纲》等课程,进行了试讲。通过学习与研修,具备了北京市高等中医教学师资水平。
1980年,我调入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从事临床、科研、教学等工作。
追溯中医学的发展历程,自《黄帝内经》以下,名家辈出,先有张仲景创方书之祖《伤寒杂病论》,后有孙思邈、钱乙、金元四大家、张景岳、叶天士、王清任、吴鞠通、傅青主等名家,历史长河中的众多医者,结合当时疾病发生的病因病机特点,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医学理论,创立了很多奇效良方。为了实现“广济苍生”的夙愿,我博采众方,熟读《千金要方》《脾胃论》《兰室秘藏》《丹溪心法》《类经》《温病条辨》《医林改错》《小儿药证直诀》《傅青主女科》等医学典籍,对叶天士、吴鞠通、钱乙、傅山等著名医家的主要学说进行了广泛的学习研究,在妇科、儿科、皮科、温病等多个学科领域都有所涉猎。治妇人病以虚实为纲,重视调和五脏,疏肝活血,调整月经周期。治小儿病注重消除积滞,健运脾胃,关注平素饮食调护,拟方投药量少力专。对皮肤病则注意通过观察皮损形态参考辨证,治疗强调以内调外,诊法、辨证和遣方用药皆有特色。
我师从“伤寒学派”,重视六经辨证。六经辨证之法,首创于张仲景《伤寒论》,六经指三阳经(太阳、阳明、少阳)和三阴经(太阴、厥阴、少阴)。发病初期,正气未衰,机体抗邪力强,反应呈亢奋状态,为三阳病,性质多偏热,属实,为腑病;若正气衰弱,机体抗邪力减弱,机体反应呈衰弱状态,为三阴病,性质多偏寒,属虚,为脏病。我认为,六经辨证实质上不外是六经所属脏腑的阴阳、气血、虚实、寒热的变化,基本病理亦与气血相关,即《素问·调经论》所云:“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气血充足、畅达,则机体阴阳平衡,脏腑经络组织功能协调,正气强盛,“邪不可干”。“正不胜邪”则发病,即《素问·调经论》云:“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故气贵贯通,血贵和畅,气血生化调和,是人身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即《丹溪心法》云:“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我始终认为,气与血二者,不可偏废,也不可偏执,而是要依靠辨证立法,气血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