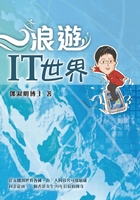
我遇上了GIS

上了香港大學,我主修自小熱愛的地理,副修經濟。那時的地理系,涵蓋的範圍很廣,包括城市規劃(urban planning)、環境學甚至地底地面的建築設計等。
二三年級時,適逢有個GlS客席教授來港大開班。聽到GlS的概念,已萌生這是世界未來的感覺——我自小學開始迷上地圖,並把各地的知識如地形、氣候、語言、文化等分門別類自製筆記。但搜集的資料愈多,愈覺得難以在一個像紙張這樣的平面上好好表達,只是未想到有甚麼更好的方法。
GIS的英文全寫是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中譯是「地理資訊系統」,它結合了地理學、地圖學、資訊科技,把數據資料與空間位置連結後,為機構和個人傳遞這些資訊,從而提升生產力。
GlS用電腦分析和整理多層次的地理資料,比紙張地圖更方便易用。那時GlS班只收20個學生,我有幸是其中之一。結果20個同學中,最終只有我一人從事GlS的工作。
畢業後,最開心是可以為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和政府整理香港第一張植被(vegetation,指覆蓋地球表面的植物)地圖,原來香港因為地理和氣候的關係,植物的多樣性更勝英國。植被覆蓋度對環境保護有指標作用,因此意義重大。當中也需要運用GlS的知識,我有機會學以致用,更感GlS的實用。其後,我又聯同香港大學生態學及生物多樣性學系的師生團隊,共同為香港建立了首個香港生態學數據庫,為香港生態學研究提供了數據資料的基礎。
製作「植被地圖」的過程中,親眼見識了香港宏觀的植被環境,香港表面上很都市化,實際上有近7成土地被植物覆蓋,樹木的高低大小也可從地圖中反映出來。這幅地圖是學術與興趣的完美結合,能夠以專業知識為社會和學術界貢獻,令我深感自豪。
我同時也在港大兼教GlS,能夠把這門學問傳揚出去本來令人興奮,可是慢慢我就發現,以教學方式並不足以把GlS發揚光大——每班極其量教導二三十個學生,即使教十年八載充其量也不過數百人,春風化雨雖然是自小的心願,但影響有限;而當時GlS仍只屬學院內的玩意,政府和商界仍舊普遍使用手繪紙張地圖,遠遠落後美加等地。
興趣結合性格特點能發揮更大的優勢,加上市場分析,我的創業決定並非一時衝動——我當時只有廿多歲,又沒有家累,大可放膽一搏。
要推廣GlS,我醒覺到自己需要離開學院,離開安全區(comfort zone),嘗試創業。回想當初,自己的心態像個農夫,原本一心只想勤懇播種,培訓更多GlS人才。但是,細想一下便知道這並不足夠,我必須同時建立一個市場,一個泉源豐沛、活水不息的生態環境,製造就業機會,讓學生能學以致用。解決紙張地圖衍生的問題之餘,發展下去,這個生態系統更可以把創新科技、創新人類和創意思維匯集緊扣在一起,進而開拓新經濟新市場,令香港發展成更具競爭力的城市。
於是,我毅然拿出全部積蓄,投入創業,全力推廣GlS。這個決定當然引來親朋戚友的反對,認為我會斷送大好前程……
當時腦內不禁浮現德國化學家、曾於1910年獲諾貝爾化學獎的奧托·瓦拉赫(Otto Walkach, 1847–1931)的傳奇故事。話說他年少時酷愛文學藝術,父母也大為鼓勵,但後來他發現自己對化學的興趣更大,也與自己一絲不苟的性格更吻合,於是他毅然全身投入化學研究,「智慧火花一下子被點燃了」,成就一個偉大的化學家。他的故事在在說明,興趣結合性格特點能發揮更大的優勢,加上我分析了客觀市場狀況,很清楚自己的決定並非一時衝動——我當時只有廿多歲,又沒有家累,大有放膽一搏的資本。
主意已決,我便展開了創業的冒險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