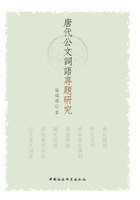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價值
一 研究對象
本文以唐代公文文獻詞語爲主要研究對象。公文是用於處理公務的官方文書。唐代公文文獻以文言語體爲主,内容貼近當時的社會生活,對唐代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作用。整體而言,這些文獻可以大致分爲下行文書、上行文書和平行文書等。《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即言:
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冊、令、教、符。〔天子曰制,曰敕,曰冊。皇太子曰令。親王、公主曰教。尚書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皆曰符。〕 凡下之所以達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狀、牋、啟、牒、辭。〔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爲狀。牋、啟于皇太子,然于其長亦爲之,非公文所施。九品已上公文皆曰牒。庶人言曰辭。〕 諸司自相質問,其義有三,曰:關、刺、移。〔關謂關通其事,刺謂刺舉之,移謂移其事於他司。移則通判之官皆連署。〕[4]
中村裕一對唐代公文文獻的研究更加系統,認爲它包括以下類别:冊書、制書(詔書)、慰勞制書、發日敕書、敕旨、論事敕書、敕牒、奏抄、表、狀、辭、議、令書、牋、啟、教、奏彈、露布、解、刺、移、關、牒、符、制授告身式、奏授告身式、判授告身式、計會式、諸州計會式、諸司計會式、過所等。[5]
冊書、制書(詔書)等都是皇帝或以皇帝名義發佈的文書,“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后建嫡,封樹藩屏,寵命尊賢,臨軒備禮則用之。〕二曰制書,〔行大賞罰,授大官爵,釐年舊政,赦宥降慮則用之。〕 三曰慰勞制書,〔褒贊賢能,勸勉勤勞則用之。〕 四曰發日敕[6],〔謂御畫發日敕也。增減官員,廢置州縣,徵發兵馬,除免官爵,授六品已下官,處流已上罪,用庫物五百段、錢二百千、倉糧五百石、奴婢二十人、馬五十匹、牛五十頭、羊五百口已上則用之。〕 五曰敕旨,〔謂百司承旨而爲程式,奏事請施行者。〕 六曰論事敕書,〔慰諭公卿,誡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敕牒。〔隨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7]奏抄,“謂祭祀,支度國用,授六品已下官,斷流已上罪及除、免、官當者,並爲奏抄。”[8]奏彈,“謂御史糾劾百司不法之事。”[9]露布,“謂諸軍破賊,申尚書兵部而聞奏焉。”[10]議,“謂朝之疑事,下公卿議,理有異同,奏而裁之。”[11]告身式是官方發佈的授官任職的文書憑證;計會式是地方官員每年年末呈送給中央的財務資料;過所是通關文書;解類似於官府呈送的考生檔案,根據選人的出身、來歷等編制而成,每州一解。[12]
二 語料簡介
現存唐代公文書見於傳世文獻和新出的敦煌吐魯番文獻,其中以詔令(冊書、制書等)、奏議(奏抄、議等)兩大類數量最爲眾多。《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五《史部》即專列“詔令奏議類”,並簡述其源流:“記言記動,二史分司。起居注,右史事也。左史所録,蔑聞焉。王言所敷,惟詔令耳。《唐志》史部,初立此門。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則移“制誥”於《集部》,次於《别集》。夫渙號明堂,義無虚發。治亂得失,於是可稽。此政事之樞機,非僅文章類也。抑居詞賦,於理爲褻。《尚書》誓誥,經有明徵。今仍載史部,從古義也。《文獻通考》始以 ‘奏議’自爲一門,亦居集末。考《漢志》載奏事十八篇,列《戰國策》、《史記》之間,附《春秋》末。則論事之文,當歸《史部》,其證昭然。今亦併改隸,俾易與紀傳互考焉。”[13]此外,告身式、過所等文書則散見於敦煌吐魯番文獻。鑒於不同形制的唐代公文文獻數量差别懸殊,根據詞彙研究的實際需要,我們將唐代公文文獻粗略分爲詔令、奏議、其他三大類。
詔令文書集中於《唐大詔令集》、《唐大詔令集補編》二書,奏議文書則多見於唐人文集。《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全唐文》等廣收有唐一代文獻,内容涉及唐代公文的方方面面。茲對相關文獻加以臚列紹介。
《唐大詔令集》,宋綬纂輯,宋敏求整理成書,“本書經歷宋元明清迄無刻本,直到光緒間才由南潯張鈞衡據明抄本鏤板行世,收入適園叢書。”[14]該書130卷,現存各本均非全帙,共闕23卷,即卷十四至二十四、八十七至九十八,存107卷。其内容“共爲九類,下分子目一百五十九,凡一千六百四十九篇,其中間有重複,卷一百二十四《平李懷光詔》、《平李希烈詔》,與卷一百二十一重見,實核 ‘詔令集’收文一千六百四十七篇,約八十六萬八千字。”[15]
現在比較通行的是商務印書館1959年排印本。該本系趙守儼先生以顧廣圻所校舊抄本爲底本,用適園本校勘,並參照四庫文津閣本及翁同龢校本。此本校勘極爲謹慎,便於使用。然而,從研究角度看,尚有微疵:第一,未出校記。“顧廣圻校語凡屬正誤性質的,大部分已據改(少數幾處未從顧校),至於和《文苑英華》比較異同的,擇其重要者,與本館校勘中所發現的疑而未決的問題合併在一起,另列校勘表附於書後。”[16]顧廣圻校語並未獨立刊出,校勘表僅一頁,異文内容過少。第二,對校所據抄本不全。除了趙先生所列的幾個本子外,大陸與臺灣尚存多種抄本。限於時代條件,臺灣所藏抄本難以採用。但未參照上海、南京、廣州所藏抄本,頗爲可惜。中山圖書館與中山大學圖書館均藏有明抄本,時代較早。詳加比勘,或更可近於該書原貌。第三,未作他校。正如《出版説明》所言:“如以《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唐人文集、《通典》、《唐六典》、《唐會要》所載詔令與本書仔細核對,一定還可以發現不少的問題。”[17]商務本並未如此做,“我們出版這部書,目的只是爲讀唐史的人提供參考資料,因此付印之前没有進行這樣的整理。”[18]中華書局2008年據商務本重新印行出版,將原《出版説明》改爲《前言》,並新附《出版説明》,正文與商務版無區别。我們想要如實地研讀該書,需要做一番校勘工作。
《唐大詔令集補編》,李希沁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標點本。《補編》共收詔令五千餘篇,去其重複,實收詔令四千餘篇,約有一百二十萬字。該書裒輯《唐大詔令集》未收之詔令而成,其《編例》云:“(二)本編補收之唐代詔令,録自《舊唐書》、《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唐會要》、部分唐人文集與《全唐文》等書,以及部分唐代石刻、唐人墓誌等。”[19]從該書編例可知,宋代類書及《全唐文》等文獻中的詔令幾乎被悉數囊括。故爲進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匯集本。該書與《唐大詔令集》體例相似,正文不出校記,文句有異同多以意逕改。故在使用時可以該書爲依託,對具體篇章按圖索驥,查核原文。韓昇、張達志《〈唐大詔令集〉補訂》,載於《傳統中國研究集刊》。這是以論文形式發表的唐代詔令彙編。其輯録所據材料以墓誌爲主,彌補了《補編》在這一方面的不足。
唐人文集存有數量較多的奏議文書,如唐代名臣陸贄《陸贄集》即有奏草奏議等十二卷。[20]就留存情況看,宋代人已經有意識地編纂出版唐人文集,至於清代,則有《四庫全書》搜羅唐人文集。中華書局《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等,點校出版了大量的唐人文集,校勘比較精善,便於使用。
《文苑英華》,北宋李昉等撰,收梁末以至唐代詩文,而以唐代文獻爲主。内中詔令、奏議文書數量甚夥,可與《唐大詔令集》、單行的唐人文集等對觀,有些僅見於此書。中華書局1966年影印宋刻本(原書一千卷,宋本止存一百四十卷,缺卷以明隆慶元年胡維新刻本補配)。《全唐文》,清徐松等編,該書凡例詳細説明其編纂體例,據凡例可知,編者將當時能夠見到的唐文搜羅一盡,詔令、奏議文書也非常廣泛。[21]中華書局1983年曾影印出版。
《通典》、《唐會要》作爲典章制度類文獻,也收有大量唐代公文。[22]《通典》,唐杜佑撰,存有許多唐代詔敕和奏疏論議等。日本藏有該書南宋刻本,並已影印出版。中華書局1988年出版王文錦等點校本,頗便使用。《唐會要》,北宋王溥撰,是書以唐人所撰《會要》《續會要》增修而成,比較貼近唐代文獻原貌。《唐會要》與《通典》類似,收有不少詔令、奏議文書的片段。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有點校本(2006年有所改訂,並推出第2版)。
《冊府元龜》,北宋王欽若、楊億等撰,此書重在以類書體例編纂歷代君臣事跡,分帝王、閏位、僭僞、列國君、儲宫等三十一部。唐五代部分,收有大量詔令、奏議文書。宋初,唐代實録、國史、詔敕奏議等尚有留存,《冊府元龜》的公文文書多直接取自這些材料,許多文字不爲其他文獻所載,具有獨特的文獻價值。不過,現存宋刻本僅剩幾個殘本。中華書局1960年曾影印明崇禎十五年黄國琦刻本,並於1989年另行影印殘宋本。南京大學周勛初先生曾主持《冊府元龜(校訂本)》,標點全書的同時,尚有詳細校記,用力甚勤,由鳳凰出版社於2006年出版。[23]
敦煌文獻包含大量唐代下行文書,可根據《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録》等按圖索驥。《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録》,唐耕耦、陸宏基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1990年初版。該書廣泛收羅敦煌社會經濟文書,每頁分兩欄,上欄爲影印的原卷,下欄爲録文。不過,釋文偶有疏失,仍需仔細核對原卷。類似的還有《敦煌表狀箋啟書儀輯校》[24]等。
此外,《玉海》《全唐文補編》等也收有許多唐代公文,因與所列各書、文内容有交叉,故不再做專門介紹。
三 研究現狀
以往學者多將唐代公文文書作爲史料進行研讀和利用,很少作爲漢語史研究的專門語料。這主要是因爲公文語言典雅、偏於文言,容易使研究者忽視其語言研究價值。不過,也有學者注意到這類文獻對漢語史研究的作用,試圖抉發其語言價值。以下簡要概述相關研究成果。
(一)史學、文學研究
史學研究主要關注唐代公文的形制、運作程式等,專書如日本學者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唐代官文書研究》《隋唐王言の研究》《唐代公文書研究》[25],劉後濱《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公文形態·政務運行與制度變遷》[26]等;單篇論文則數量極多,如戴建國《唐格後敕修纂體例考》[27],李錦繡《唐“王言之制”初探——讀〈唐六典〉劄記之一》[28],雷聞《從 S.11287看唐代論事敕書的成立過程》[29],魏斌《“伏准赦文”與晚唐行政運作》[30]《唐代赦書内容的擴展與大赦職能的變化》[31],禹成旼《試論唐代赦文的變化及其意義》[32]《唐代赦文頒佈的演變》[33]《唐代德音考》[34],張啟安《唐代公文制度研究》[35]等。
也有注重編制目録或文獻考訂者。日本學者池田溫曾編訂《唐代詔敕目録》[36]、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究》等涉及敦煌吐魯番所見公文書的綱目。由於詔敕比較集中,這方面的校訂文章較多,如党秋妮《〈全唐文〉(晚唐詔敕)考辨》[37],羅妮《〈全唐文〉唐代宗李豫詔敕考辨》[38],王士祥《〈唐大詔令集〉系年辨誤》[39]《〈唐大詔令集〉系年糾謬》[40],郗政民《〈唐代詔敕目録〉求疵》[41],趙俊《〈唐大詔令集〉勘誤二則》[42]等;對奏議等文書的校訂内容則散見於各類文集的點校本中,系統的論著相對較少。
文學方面,主要涉及詔令、奏議文體的研究,如冷琳《論隋至中唐駢體公文改革及陸贄的傑出成就》[43],孟慶陽《唐代奏議文研究述評》[44]、《唐代奏議文研究》[45],寧薇《唐代駢體公牘文論稿——以陸贄爲中心》[46],熊碧《唐代奏議的文學研究》[47],徐泰琳《陸宣公詔書研究》[48],張超《唐代詔敕研究》[49]、《詔敕文體改良與中唐古文運動》[50]等。此外,還有些公文研究成果散見於唐代專人研究論著之中。
(二)語言學研究
目前專門研究唐代公文的語言學著作還不多見,僅有數篇碩士論文,包括杜征《韓愈散文複音詞研究》[51],侯璐《唐代奏議文語言特點研究——兼與現行報請類公文比較》[52]等。更多的研究論著是將唐代公文作爲參證材料,如王啟濤《吐魯番出土文書詞語考釋》[53]就涉及不少唐代公文,丁聲樹《“早晚”與“何當”》[54]、真大成《關於常用詞“腿”的若干問題》[55]也都引用唐代公文來解釋語言演變問題。
四 研究價值
研究唐代公文詞語對於斷代語言研究、史學研究、辭書編纂等都有重要價值。
(一)斷代體裁語言研究
呂叔湘先生曾指出:“以語法和詞彙而論,秦漢以前的是古代漢語,宋元以後的是近代漢語,這是没有問題的。從三國到唐末,這七百年該怎麼劃分?這個時期的口語肯定是跟秦漢以前有很大差别,但是由於書面語的保守性,口語成分只能在這裏那裏露個一鱗半爪,要到晚唐五代才在傳統文字之外另有口語成分占上風的文字出現。”[56]
晚唐以前“口語成分占上風的文字”少見,而唐代正是文言與白話轉變的重要時期,對該時期語言面貌的整體把握有助於漢語史的歷時研究。唐代公文貫穿有唐數百年,大多數文書的寫作年代極爲明確,其内容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文書起草者中不乏久負盛名的文士,如張説、蘇珽、陸贄、元稹、白居易等。
唐代公文通過長期發展,形成了以文言爲主而夾雜時語的文體面貌。在這幾百年間,公文作者面對相似的題材,留下衆多異代同題的語料,其詞彙、文法的通與變必有可觀之處。唐代不少皇帝愛好文學,當時也通過科舉策對選取了許多優文之士。帝王以進士科爲優學的表現,如唐宣宗即自許爲“鄉貢進士李道龍”[57]。由於這些帝王有一定的文學素養,部分公文的寫作水準就很可能影響撰者的仕途[58]。整個唐代,各類公文的體式變化不是很大,撰者要展現其個人的文采學識,需要在字詞、文句上著力。據我們初步考察,公文裏出現了大量的新詞。這些新詞有多種來源:當時的口語詞以及文人造詞,二者都佔有較大比重。
文人造詞對實際語言的推動力究竟如何,還是值得繼續探討的問題。真大成《中古新詞“不涯”考釋》一文談及“不涯”時有以下論斷:“論其來歷,很可能出於文人之手,是文人行文遣辭創新的結果。事實表明,中古時期不少新詞的出現、新義的衍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人的書面創作。這些語言新質極可能没有自然口語的基礎,大抵行用於書面文獻,生命力或强或弱,延用時間或長或短。文人的書面語創作與使用對於漢語詞彙化、豐富漢語詞庫、促使詞義變化等方面均有重要作用。因此,對於書面文獻極其充盈的漢語而言,除了挖掘其中的口語性材料、探究口語詞彙現象外,那些産生于文人筆端、具有書面語色彩的語詞也應是漢語詞彙史研究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對象。”[59]唐代公文包含大量的文人新造詞,有深入考察之必要。
現階段,唐代俗語詞研究更爲充分,而文言文獻詞語研究相對薄弱,“過去人們的研究,或表現出重 ‘語’輕 ‘文’的現象,或著眼於專書詞彙的研究,對體裁語言的研究關注得很不夠。”[60]公文語言正是重要的體裁語言。研究唐代公文詞語,有利於全面了解唐代語言的整體面貌。
(二)史學研究
史學研究的重要基礎就是詞語考釋。何茲全、陳琳國在評價《魏晉南北朝史札記》的貢獻時就提道:“有關魏晉南北朝的十二部 ‘正史’,由於缺乏考釋訓詁之作,其中的許多史實、制度、名物、語言等,今人已不甚了了。這種狀況給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特别是青年學人的研究工作帶來不少的困難。因此,考釋十二部 ‘正史’無疑是一項迫切而又艱巨的任務。如今,這個任務終於由學兼中外的著名史學家周一良先生擔當起來,並且部分完成了。”[61]同樣的,歷代的公文等也缺乏訓詁考釋之作。考察唐代公文詞語,自然有利於唐代史學研究的深化。
如果沒有對詞語的準確考釋,很容易影響對具體問題的判斷。《唐六典》卷九《中書省》“中書舍人”職掌條注云[62]:
其中書舍人在省,以年深者爲閣老,兼判本省雜事;一人專掌畫,謂之知制誥,得食政事之食;餘但分署制敕。六人分押尚書六司,凡有章表,皆商量可否,則與侍郎及令連署而進奏。其掌畫事繁,或以諸司官兼者,謂之兼制誥。
張東光《唐宋的知制誥》認爲此“知制誥”是“職”:“唐代前期中書舍人中直接同政事堂、皇帝聯繫的知制誥,是中書秘書班子中的關鍵人物,相當於後世翰林學士中的 ‘承旨’學士。此職獨承密命,‘給食於政事堂’,乃學士院出現以前,舍人中掌 ‘内制’者。”[63]而賴瑞和《唐代三大類型知制誥的特徵與區别》“知制誥的雙重含義”部分則認爲此“知制誥”爲動賓短語,猶言“掌制誥”,“此處的 ‘知制誥’不是這位中書舍人所帶的使職官名,只是他負責的職務”[64]。可見,各家意見並不一致。對此處“知制誥”的理解影響到唐代中央官制的研究問題。其實,唐代知制誥有三種意義,此處“知制誥”是指“中書舍人中專掌制誥者的專稱(别名)”。明乎此,才能更準確地研究唐代中央官制。
(三)辭書編纂
“語文辭書的編寫以詞彙研究爲基礎,同時,又反過來推動詞彙研究的深入。漢語詞彙的研究至今還比較薄弱,許多詞似懂非懂,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65]研究唐代公文詞語,有利於辭書編纂,可補訂範圍不僅限於一般辭書(如《漢語大詞典》),還包括專類辭書(如官制辭典、職官别名詞典等)。以下僅舉數例説明。
1.增加新詞
有些詞語在官制辭典、語文辭書等中都未加收釋,但又明顯屬於“字面普通而義别”的新詞,理應加以補充。以“十乘”[66]爲例,“十乘”本指十輛馬車,唐代公文有以下用例:
(1)將有事於四方,且申爾志。俾啟行於十乘,式佇其能。(《唐大詔令集》卷三六《奉節郡王适天下兵馬元帥制》)
(2)爾其弘樽俎之嘉謀,念折衝之遠略。寵膺十乘,位列三台。(《唐大詔令集》卷三六《濮王澤成德軍節度制》)
(3)輟于三台,先以十乘。不改巖廊之任,用資垣翰之光。(《唐大詔令集》卷五四《王摶威勝軍節度平章事制》)
顯然,不能簡單以十輛馬車索解“十乘”的意義。推敲可知,“十乘”截取《詩經·小雅·六月》“元戎十乘”而成詞,代指“元戎”,義爲主帥或先鋒。
2.補充新義
有些詞語雖然辭書已經收釋,但通過唐代公文詞語的研究,可以補入新的義項。唐代公文有“刻舟”[67]一詞:
(1)刻舟敏遽,牽衣慧早。(《唐大詔令集》卷三二《懿德太子哀冊文》)
(2)智有刻舟之妙,辨多對日之奇。(《唐大詔令集》卷三三《封棣王祤等制》)
(3)刻舟志邁於蒼舒,占雨識高於沛獻。(《唐大詔令集》卷三六《濮王澤成德軍節度制》)
《漢語大詞典》收釋“刻舟”,其義爲“‘刻舟求劍’之省”[68]。但深入推考,此處“刻舟”蓋指三國曹沖刻舟秤象事。由於曹沖小小年紀就能設法稱取巨象的重量,所以往往以此事比喻人年少聰穎。因此,應增加義項:指三國曹沖刻舟秤象事,喻指人年少聰慧。
3.提前書證
有些詞語雖然辭書已經收釋,但所舉例證時代較晚,可以利用唐代公文提前書證的年代。如“察訪”“給付”等。由於電子語料庫的普及,進行提前書證的工作較之此前更爲便利,本文就不再作過多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