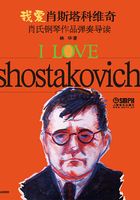
3.认识专政
由于新政策的宽容,肖斯塔科维奇很快崭露头角,甚至也为欧洲乐坛所知晓。但是这段时间并不长。可怜的初生牛犊还不知道何谓苛政者的虎威。这一厢情愿的创作热情,很快被风吹雨打去。1932年苏联当局加强了对艺术的控制。1934年肃反清洗开始,大批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1936年开展了对他的点名批判。
出于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虔诚的肖斯塔科维奇也相信自己是错误的,并按照传统的章法写了《第五交响曲》(1937),作为自己对“正确批评之后的回答”。这部作品使他得到当局的谅解,于是,他的以往声望又得到恢复了。在这段时间里还写过被西方评论家认为“守旧的”[7]《第六交响曲》(1939)、《第二钢琴奏鸣曲》(1942)等,但是这些作品无论在国内国外都没有得到好评。
在卫国战争中老肖写了《第七交响曲》而举世闻名,并且得到前所未有的国际荣誉。但是自从1936年之后,苏联的当权者就把意识形态中的一切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提到纲举目张的头等重要地位,因此卫国战争刚过,对于思想文化艺术方面的控制就立刻升温。意识形态专家日丹诺夫[8]被委以重任,1946年开始对电影的批判,1948年他也没有放过音乐界,把肖氏再次揪到光天化日之下,作为形式主义作曲家的代表人物再一次加以口诛笔伐。
这时候的肖斯塔科维奇是否还像他30岁时那样心服口服,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此后他的创作就采用两种音乐语言:一种是面向广大群众的,那都是一些在思想上绝对是无可争辩的作品,如电影配音《青年近卫军》《攻克柏林》以及《森林之歌》等。一种则是为着自己所设定的艺术命题的写作,如《二十四首前奏曲与赋格》《钢琴二重小协奏曲》(1953)和《第二钢琴协奏曲》(1957)等等。

美国《时代周刊》封面:肖斯塔科维奇

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日丹诺夫

1905年苏联的革命海报

捷杰耶夫指挥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的CD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