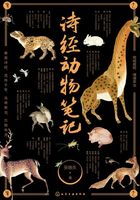
犬:凸显了人的孤独

查小三家南侧有一排青砖黑瓦屋,似是这座清末地主庄园当年专给仆人居住的寝室。现在想来,那屋子造得也用心——地板之下的墙脚,还开几个对外的洞口。
一天,我隐约听见洞口传来动物的声音,低头往里瞅,竟然与一双黑溜溜的眼睛对视上了!
小狗狗!
校园里那只无主母狗生小狗啦!
伙伴们很快都知道了,纷纷围过来。我们想方设法将小狗狗引诱出来,抱着玩。而母狗可怜兮兮地跟着我们,生怕弄坏了它的娃。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还没有“宠物”概念,狗的品种很少,通常都是中华田园犬——土狗。
跃跃毚兔,遇犬获之。
(《小雅·巧言》)
祖先们用狗猎兔,场面一定很壮观。土狗跑起来比不上真正的猎犬,所以,祖先们肯定是带了一群土狗,在原野上奔驰围剿。可以想见:野兔和狗踏出的烟尘,使荒野起了一层雾,大呼小叫声里,还惊起一群野鸡、鹌鹑。那种丰美与鲜美,纵横整个《诗经》作品诞生的五百年。

我目前陪读租住的房门前电梯边,长期锁着一条黑狗,是隔壁老先生的。它不是纯种土狗。性情温和,特别懂礼貌,从不乱叫。只有老先生将它牵到楼下树边拴着时,它看到我才会汪汪大叫,头贴地,两只狗眼深情地盯着我。那意思按照动物行为学家的说法,是极力邀请我陪它玩耍。
我和这只狗关系非常好,甚至可以掰开狗嘴,查看它的犬齿。有学者说,狗是狼5万年前演变的。而中国最早的狗出现在吉林榆树县周家油坊地层下,是个头骨“半化石”。它生活于公元前2.6万年至公元前1万年间,也可能是旧石器时代的家狗遗骸。
祖先们对狗情有独钟,打猎、看家是主要用途,另有一用就是做火锅。很多西方人不喜欢中国人吃狗肉,因为他们视狗为朋友,乃至家庭成员。这一点我深表同情,我绝不吃狗肉。不过,真要从伦理学层面找依据,也很难。毕竟我们不能把狗的地位提高到猪、牛、羊之上。不要以一只狗或一只猫为出发点,去伤害别人。这是反伦理。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陶渊明《归园田居》)


——人类生活越简单,越体现真诚淳朴的伦理。伦理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其实有点“过分”。因为它把人类伦理弄复杂了。一般人绝不可能通过各种《伦理学》去学习伦理,还不如像陶渊明那样听听狗吠、鸡鸣——这就处在最好的伦理状态。当人们为伦理而争辩的时候,伦理其实已经淡化了。
狗不懂伦理,但似乎懂得爱。它对它爱的人,可以付出一切。“左牵黄,右擎苍”的古人,与狗融洽相处,虽然视它为打猎工具,但彼此间有一份单纯情义。因为深入人的生活,古代文化中,狗的影子无处不在——
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
(《刺巴郡守诗》)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十五从军征》)
——两句汉代诗歌,并没有对狗做价值或道德判断,只是营造一种紧张,一种凄凉。人间事其实与狗无关,但又深切相关。它们用狗的意象,体现人的悲哀与落魄。作为人的附属物的狗,在繁荣的时候,可能也对应了人世的幸福。
但当代社会推翻了这个观点。虽然狗数量多,种类纷繁,却凸显了人的孤独。
陪伴人千万年的狗,是最合群的一种动物。我儿时与伙伴们玩弄那只校园无主母狗的娃娃时,它没有凶狠护崽,只是不放心地跟随我们。因为我们平时就好在一起玩耍,它视我们为朋友。从这层意义上说,人类反过来视狗为朋友也是正确的,这是培养爱的一个机会。
当人与人之间戾气增多的时候,人其实不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