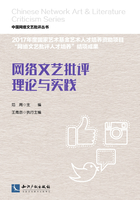
二、回归:“后人文主义”的价值倾向
诚然,“后人文主义”与网络文艺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还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做出这样的假设,即“后人文主义”完全有可能成为网络文艺的价值参照,尽管这一假设的正当性和可能性在后文注定还要加以必要的论证。
在论证这一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阐述的是,“后人文主义”作为一种学术话语有着什么样的价值内涵。如果缺乏这一论述的基础,那么也就很难进入到对“后人文主义”与网络文艺之间关系的讨论。已经可以确信,“后人文主义”不意味着对“人文主义”的全盘否定,事实上,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也完全没有必要提出“后人文主义”这样一个概念。顾名思义,“后人文主义”总还是与“人文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人类理论的领军人物、美国莱斯大学教授卡里·伍尔夫(Cary Wolfe)不仅肯定了“后人文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积极友善的关联,同时也曾经试图界定“后人文主义”的价值内涵,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后人文主义”并不是对人文主义的拒绝,也未否定人文主义的价值,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得面临挑战的诸如正义、宽容、公平、高尚、人权等的人文主义价值,再度熔铸成为人类特性的内在组成部分,由此来探究人文科学的谱系。![刘悦笛.后人类境遇的中国儒家应战——走向“儒家后人文主义”的启示[J].探索与争鸣,2017(6).](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79C9D5/145728055044986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8826287-3L5HtbG3n2HSMQNskUEXhjyXqnY0tJ8S-0-184379ee88bc0d30e28d8559ef50844b)
于此,卡里·伍尔夫至少肯定了讨论“后人文主义”的价值内涵的可行性,他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便利。需要辨别的是,难道“后人文主义”在价值层面仅仅只是延续了“人文主义”的固有命题、所不同的只是这些命题面对着的历史条件?似乎事实并非如此。
下面讨论的几个关键词在某种程度上呈现着“后人文主义”在价值层面具有代表性的取向。
(1)生态。如果说物理学曾经作为自然科学的主要代表,为人文学科输入了大量到目前依然还在运用着的思维范式和思想观念,那么到了20世纪末期,生物学、生命科学以其独到的魅力取代了曾经一度辉煌的物理学。从这个时候开始,人文学科不再满足于从物理学等纯粹抽象的、逻辑的自然科学中吸取、借鉴,而是以无比的热情关注着一切与生命自身有关的学科,于是“生态主义”随之成为一个越来越具有某种公共性、普适性的学术热点。不仅如此,在人文学、生态学的深度对话中,诸如生态人类学、生态史学、生态哲学,后来又产生了生态美学、生态媒体和生态电影、生态语言学、生态诗学、生态评论、生态符号学、政治生态学等一系列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领域随之涌现,并且也无一例外地成了这个时代的显学 。人文学科之所以会如此看重生态学,其深层的原因无非是生态学可以保证我们能够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看待生命、看待世界、看到我们自身以及与我们自身相关的一切事物。在现代主义、人文主义的语境中,人以及人生存其中的这个世界无疑是清晰可知的,只要通过一定方式获取到并掌握某些原理、定律,那么所有这一切不仅是可知的,同时又是可以操控的。但生态学很快否定了这一点。生态学告诉我们,无论是人还是这个世界,其复杂性、神秘性都远远超过我们的认知,我们其实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更加让我们难以接受的是我们其实对自己也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生态学首先告诉我们面对这一切要学会心怀敬畏。在敬畏中感受、领会人类自我以及世界万物的奥秘,当我们的认知因此而有所扩展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行为随之有所调整。可以说,“生态主义”是“后人文主义”最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部分,因为“生态主义”不仅使得“后人文主义”获取了独特性,同时也塑造了其人文价值形象
。人文学科之所以会如此看重生态学,其深层的原因无非是生态学可以保证我们能够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看待生命、看待世界、看到我们自身以及与我们自身相关的一切事物。在现代主义、人文主义的语境中,人以及人生存其中的这个世界无疑是清晰可知的,只要通过一定方式获取到并掌握某些原理、定律,那么所有这一切不仅是可知的,同时又是可以操控的。但生态学很快否定了这一点。生态学告诉我们,无论是人还是这个世界,其复杂性、神秘性都远远超过我们的认知,我们其实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更加让我们难以接受的是我们其实对自己也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生态学首先告诉我们面对这一切要学会心怀敬畏。在敬畏中感受、领会人类自我以及世界万物的奥秘,当我们的认知因此而有所扩展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行为随之有所调整。可以说,“生态主义”是“后人文主义”最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部分,因为“生态主义”不仅使得“后人文主义”获取了独特性,同时也塑造了其人文价值形象 。
。
(2)传统。“后人文主义”并不否认“向前看”,只是认为在“向前看”的同时也有必要“向后看”,而“向后看”曾经是让现代主义者、人文主义者颇为反感的。不过,让现代主义者、人文主义者意想不到的是,他们会为他们不恰当的反感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前车之鉴是必须要汲取的。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后人文主义”开始对人类的过去以及人类过去所做的一切、所想的一切满怀敬意。在这里,传统这个词不会再与落后、腐朽、没落、守旧等很多负面性较强的判断联系在一起。在经过重新的审视之后,传统被赋予了智慧、创造、源流、归宿等更为积极的含义,这在现代主义者、人文主义者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现代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坚持“向前看”时候,他们其实内在地坚信,在探究的尽头,会有他们所期待的一切美好等待着他们。但不幸的是,人类的智慧终于发现并承认,在我们的前面,除了我们无法掌控的虚空之外,其实真的一无所有。而这广袤虚空的沉重是我们人之为人很难肩负起来的。更为致命的是,这虚空的宿命我们没有理由躲避。或许,回归传统是唯一的选择。也只有传统,才先天具备在虚空中立足的坚韧和力度。基于对传统的回望,“后人文主义”在价值观层面上多了一重历史的沧桑与厚重。我们其实应该追问的是,除了历史的沧桑、厚重,传统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当然不只是所谓的经验和教训。确切地来讲,传统为我们的生命构建了一个境域,经由传统,我们能够得到人之为人、世界之为世界的全部规定性。回望,不一定意味着退守。的确,“后人文主义”对传统会有新的期许,但“后人文主义”也不会以任何方式胶着于传统的某个角度、某个片段。
(3)生活。很难说,是不是只有人类才会有探问真实的冲动与尝试。但就目前所见,确实只有人类这个群体不满足于本然的存在状态,不断尝试询问着、构建着具有恒定而可信的“真实性”。人类文化中的这种“真实性”因素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一种是彼岸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对自身生存的短暂和不稳定满怀忧虑,而他们对外在于自己的整个世界的神秘和强大知之甚少,在他们看来,有一种比人的力量更为强大、更接近永恒的世界存在着。这时的人类设想,如果有办法接近这个世界、得到这个世界的力量,那么就相应地把握住了真实。于是,一个有神的世界诞生于人类的文明实践中;另一种是理性的、逻辑的世界。当人类开始对自身以及外在的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知之后,至少有一部分人不再相信会有那样一个曾经让自己无比狂热虔信的神圣世界,相比之下,对理性力量的肯定转而让追寻真实存在感的人类对理想的世界有了新的认知、新的期待。通过理性的审问、逻辑的推演,一个不同于带有神性的彼岸世界的新的世界观诞生了,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似乎拥有了真实的目标、真实的方法、真实的路径等;再等到人类对彼岸世界、理性世界都不再信任的时候,能够表示信任的似乎只有一个感性的世界了。带着对重新发现人的感性的无限欣喜,通过艺术,人类再次给自己创造了一个似乎绝对可信的纯粹的美的世界。但不幸的是,人类对于真实的渴望同时破灭于这三重世界。除了对真实的渴望不用怀疑,似乎其他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其实,在构建这三重世界的时候,人类同时忽视了一个最为真实可信的因素,即人的生命不断展开着的、由人的思和行共同组成的现实生活世界。遗憾的是,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历史中,最不为人类所信任的恰恰就是我们的生活。“诗和远方”固然值得追求,但不应该忘记的是,“诗和远方”总有一个起始的点和回归的点,这个点就是生活。而生活也正是“后人文主义”开始的地方。
虽然不能说生态、传统、生活这几个关键词就全然昭示了“后人文主义”的全部价值内涵,但至少也表征着“后人文主义”某些重要的价值倾向。由此不难看出,“后人文主义”的价值思想中明显体现着一种“回归”的趋向,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回归真实”的趋向。因为,在“后人文主义”这里“真实”被赋予了全新的价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