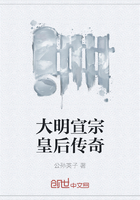
第94章 回京
第九十四章回京
听过老管家沈森述说的,这番亲身经历的他与故主人沈万三最后的岁月。望着沈海波忍不住泛红的婆娑泪眼,朱瞻基心情沉重又无言以对,不知道该如何出言安慰他,只慢慢伸出一只手臂拍在沈海波的肩上。好像唯有这样才能传递出一点,自己作为朱家的一份子的愧疚和无奈,才能稍稍安抚些自己的好兄弟那颗受伤的心灵。
孙倾城清澈的眼眸扫过这二人的面容,她能感受到这两个男人此刻心中难言的哀痛和震撼,便款步走近轻声地规劝到:
“殿下,沈兄,时辰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
“嗯。---”
“好。”
二人一起答应。
一行人迈步缓缓下楼,倾城拉住了朱瞻基的手,温润而宁静的感觉瞬间融进了朱瞻基的心底,驱散了刚刚缠绕在心中的那些许茫然和沉甸甸的不安。
眼神中略带伤感,又似有些惶惶然不知所措的无情和无心,双双跟随在沈海波身后,他们默默而行。走出很远了,依稀还能听得见,楼上学屋里传出的孩子们朗诵《论语》的读书声: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小路平坦宁静,道边枯叶随风卷起,不远处的小河岸边仍有几只不知名的五色花朵在迎风摇动绽放着芬芳,他们渐行渐远。
“唉!---”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花叶、枯木却往往比那些沉重高大而神秘的金石佛像来的更现实更具体有意义。因为它们的渺小、真实、朴素,昭示着这个世界万物有灵,人人活得不易,众生皆有悲苦。
孙倾城脑海里又浮现出佛光寺里见过的那位母亲的表兄,样貌端庄慈祥而睿智却将一生常伴青灯古佛的了悟法师。可谓天下之大,路有千条,人生在世,不如意者八九,如意事只有一二。
她几不可闻的一声叹息,打破了沉闷的气氛,几个人立即将眼光看过去。孙倾城一身淡淡的碧色衣裙,未施粉黛,青丝随风飘忽,清纯如少女般,显示出一种纯天然的美,似芙蓉出水似雨打海棠,她美的出尘入画偏又不动声色,朱瞻基望着她幽深的眼眸里透出掩不住的爱恋。只听她缓缓而言: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古往今来世间事难免谬误,多少人为此付出了可悲可叹的沉重代价。前人蹉跎,后人知警,往事已难以挽回,但可为后事之师。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却可以改变自己。期望未来会更美好一些。”
朱瞻基望了倾城一眼,点头接言道:
“说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圣人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是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唐太宗李世民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此金玉良言也。”
倾城遂用力握了握朱瞻基的手贴耳温言:
“圣主担天下重任,系万民安危于一身,需慎之又慎。倾城期望太孙殿下将来引以为戒,勿要重蹈前辄。亲君子远小人,勤政爱民,敢为天下人做主,能够做一位武能定国,文能安邦,以仁德治天下的有道明君!”
朱瞻基听了心底不由得一颤,将来自己只能做个有道明君了吗?舍弃自己从小就有的做个寻常人的梦想,不能再与心爱的倾城常住在这屯堡之中,早晨睡到自然醒,去随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难道这就是命中注定的舍得,得就有舍,舍才能得?却不知那个人人皆敬畏的皇权宝座,是如坐针毡,耗尽心力,高处不胜寒。朱瞻基扪心自问,尽管自己一直是以朱氏血脉而自豪,也向往治国以公平正义,仁德爱民。但那因“蓝党谋反案”冤杀的两万个活生生的灵魂,二公十三侯,开国大将军蓝玉、景川侯曹震,以及因无端被诬告陷害而死的顾学文一家,凄美哀婉的梁媛,沈万三和他的子孙们,都已化为森森白骨。他们有平反昭雪得到补偿的一天吗?作为朱氏子孙,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而漠视这些英灵的冤屈何谈做个有道明君?但若是要先祖皇帝蒙羞承担杀错人的罪责,不肖不孝的朱氏后人还有何面目立于朝堂之上!恐怕任何人也难以承受如此之重,建文帝不能,皇爷爷不能,父王不能,将来自己就能吗?---。
再说任何朝代的内政外邦是靠讲道理施仁德就可以解决一切的么?当然不是。因为靠慈悲和讲道理是无法千秋万代的,所以有时候逼不得已就必须要有些强硬手段,一刀见血!试问,哪一位所谓的有道明君他的手上没有沾染上鲜血?人人都说皇爷爷朱棣残暴,那个只做了四年皇帝就被夺了大位不知所踪的建文帝朱允炆仁德,可是,难道不正是他踏着万千人的尸体登上皇位,又踩着千万人的血迹亡命海外的吗?
“太孙殿下!---”
沈海波躬身揖手,他的话语打断了朱瞻基的沉思,只听他语气凄凉而不无遗憾的出口说道:
“先祖沈万三最后的遗愿是落叶归根,有朝一日能将他的遗骨迁葬回家乡苏州周庄的银子浜湖底,可银子浜湖现在是一片汪洋,想要在其水下建穴安葬他老人家怎能办得到?看来我作为沈氏后人也只能做个不孝子孙了。”
“嗯,---”
朱瞻基思量着正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孙倾城却一边插言道:
“沈兄不必忧虑,吉人自有天佑。古人曾言东海曾经数次变为桑田,是为沧桑巨变。想来贵先祖兴国公老大人生来富贵,故去又被尊为我中华财神,他的遗愿顺天宜人势必非凡,一定能够达成!”
“谢娘娘吉言!”
沈海波闻之眼中酸涩心下感激,自与孙倾城在秦淮河相遇以来,觉得她对自己总有一种自然的善意,得她诚心以待处处维护。不但促成了自己与无情小姐的两心相悦,使自己找到了知己,还得知她本是无情姐俩的救命恩人。平日里看她身份贵重从不妄言,现在听她如此说话,口吻还说的如此肯定,虽明明知道这事恐难以实现,却依然愿意相信她,心里顿时感到了莫名的满足和安定。朱瞻基也笑着点了点头,他和沈海波一样,认为孙倾城此言不过是善意的安慰。只有能预知未来的孙倾城自己知道,虽然她不能在众人面前说出口,但若干年后这就是事实。
六十年一个甲子,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太遥远。大明弘治11年,(1498年)这一年的大旱,令江苏周庄的银子浜湖水终于干涸见底,沈万三的五世孙,沈海波的重孙沈安率子沈博及女沈琼莲前往云南福泉山将先祖沈万三的遗骨运回了他发迹地的故乡古镇周庄,灵柩葬在了银子浜土下。几日后天空忽然云雾翻滚大雨倾盆,连江数日山洪暴发,江涛汹涌,银子浜湖水立刻爆满。沈万三不与世人争一寸土地,一丝阳光,一缕空气的愿望得以实现。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读史。沈万三的故事在民间口口相传,著名的山东潍县坊子木版年画就有一幅这样的沈万三聚宝盆年画,上有额书,是一首诗;“河南(黄河南边)沈万三,打鱼在江边,打着龙王宝,赚的银钱如泰山。”
“哒哒!”“哒哒!”,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官道上腾起一股烟尘,几骑俊马疾弛而来,眨眼之间便来到跟前。
“报!---”
“太孙殿下,末将幸不辱命!”
送来的是宫里发给皇太孙的六百里加急军报。两位送信的特使身负皇命一路不顾饥渴,换马不换人,日夜兼程的疾奔。他们满面疲惫一身尘土的滚鞍下马,双腿因长时间的路途颠簸僵硬的失去知觉而重重的摔倒在地,却仍坚持着双手将插有红色令箭密封的牛皮竹筒高高的举起,沙哑着嗓音递到皇太孙朱瞻基的手里才昏死过去。
身旁侍卫立即过来将特使抬去救治,朱瞻基验过漆封打开军报,明黄色的锦绢上是皇爷爷的朱笔,只有八个字:北疆战事,即刻回京!
已经过了立冬,即使是气候温暖的云南,在一早一晚间西北风刮过来的时候也是寒风似刀,人们在风中站久了脸就会粗糙皴裂,留下细小的皮肤裂痕感到干燥疼痛。为了明天一早启程,玄武和朱雀的一干手下有条不紊的先行布置着路途的护卫军务。俗话说“穷家富路”,老管家与明太医也正在带着沈海波、无情、无心和英宁积极的忙活着收拾上路的行李,准备足够的饮食、必须的洗漱和护肤用品以及常用的药物。
就要离开了,古朴秀丽的天龙屯堡。
皇太孙朱瞻基任由孙倾城拉着他的手走到夜晚的院子里,看到月光洒在她的脸上,如同一种圣光照耀着她,朱瞻基心里便感到静谧和满足。他喜欢孙倾城像小时候一样拉着自己的手,感觉她的温软,看着她不再惧怕任何的眼神,堂堂正正的和他站在一起,这就是他们一直追求的幸福。朱瞻基觉得此刻心和身无比的洁净,不染一点尘埃,只有眼前的这个女子占满了他的心田,从来没有过的充足、踏实。
“倾城---”
朱瞻基倏然俯下身,低声耳语。
“我上辈子,一定是做了一件好事,所以今生才能遇见你,得到了你。”
听到朱瞻基的情话,倾城欢喜之中又有些警惕,
“太孙殿下,就会说这种酸话,你又打什么坏主意?”
“哈哈哈!”
朱瞻基大笑,眼睛弯弯,快乐非凡,像只啄木鸟飞快地凑近倾城在她面颊上狠啄了一下。
“是有了一个坏主意,倾城,你想不想听听?”
倾城扭了扭身子,微微撇了撇小嘴,说:
“我才不要听---唔---”
朱瞻基忽然抱紧她的脑袋,吻住了她,仿佛是食髓知味二人越吻越是缠绵,久久之后才放开。朱瞻基却是叹了一口气,有些内疚的说道:
“倾城,本来是想在这天龙屯堡多待些日子的,没想到皇爷爷有旨必须回去,北疆不稳,朝中怕是有战事。你是不是觉得很遗憾?那咱们以后再来?”
倾城微微一笑,脸上被啄出的红晕尚未退净急忙摇头摆了摆手:
“没有,不妨事,已经很难得尽兴了。保国安邦是大事,太孙殿下肩负重任,我们应该以国事为先尽快奉旨回京。”
“倾城,你最好了,没有人比你好。---”
朱瞻基连想也不用想的脱口而出,这句他似乎说过了无数遍的情话。
倾城翘起唇角声音圆润娇憨:
“殿下,您正在变傻。”
哦,是了,前些日子就嫌弃本殿下老了,现在又笑夫君傻,还真是敢说!看来是得重振夫纲了!
朱瞻基心下思忖眼睛一亮,并不生气,却不怀好意地说:
“是吗?你确定?要不要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