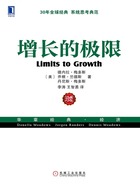
译者序
《增长的极限》一书的第1版面世于1972年,甫一出版就受到极大的关注,也引起极大的争议,后被陆续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发行数百万册。
我最初接触这本书是1993~199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全球环境与发展高峰会议”刚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闭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迅速传到中国,正是可持续发展研究最热的时候。我当时的研究方向是社会经济系统分析,在导师的指导下学习了系统动力学方法并应用于研究工作中,也阅读了《增长的极限》一书。
初次阅读此书给我带来的震撼至今记忆犹新。此前,作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在校大学生,我跟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对国家、对世界、对民族、对人类充满着关怀,喜欢思考、谈论这一类的“大”问题,总的来说充满着乐观的情绪和美好的憧憬。虽然偶尔也谈论诸如“地球末日”“人类灭亡”这一类话题,但总觉得,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那是非常非常遥远的未来,完全是一种假说。特别是当时的中国,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的鼓舞下,经济上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人们对中国的前途、对经济增长的前景充满着期望。
但是,读了《增长的极限》一书之后,我突然感觉到世界真的是有末日的,并且这个末日竟然离我们并不遥远。作为一个经济学的研究生,我突然发现原来经济增长也并不完全是件好事,不仅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还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后果,甚至可以说,增长并非如同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将把人间变成天堂,相反却可能带入地狱。
现在看来,这些想法是从一种盲目的乐观一下子走到了极端的悲观,并且这些想法本身也充满了对《增长的极限》一书的误解(这些误解后面还要谈到)。在这里回忆这些只是想说明这本书当时对我个人观念带来的巨大冲击,并且我相信,这种巨大的冲击绝不仅仅体现在我作为一个读者的身上。当时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我也常常能听到一些同学对此书的争论,反对者的观点正如那些主流观点一样,有人认为“零增长”的观点荒诞不经,将把发展中国家锁定在贫困中,也有人认为技术的发展能解决一切问题,对所谓的“极限”根本就不需要担心。
许多年过去了,硕士毕业后的我很少再想这方面的问题,《增长的极限》对我思想的冲击也慢慢淡了下来。当偶然听到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准备翻译出版2004年的《增长的极限》一书时,我立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主动请缨翻译此书。这大概也是一种情结吧。
《增长的极限》第一次提出了地球的极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限的观点,对人类社会不断追求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和警告。当时正是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社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而达到这一轮增长的顶峰,也正处于“石油危机”的前夜,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所弥漫的乐观情绪远比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时的乐观情绪更为强烈。《增长的极限》一书的问世不啻当头棒喝,本该把人们从梦中惊醒。然而,随之而来的更多是各种批判和质疑,经济学家更是对此大加鞭挞。即便是石油危机的爆发和随后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放缓,也没有被视为《增长的极限》一书的注脚,经济学家更愿意根据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做出解释。其实,当时作者只是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可能会达到这样一种极限状态,并且对达到极限和增长终结的时间,也做出了相当乐观的估计——最悲观的估计也在2015年之后,也就是《增长的极限》面世四十多年之后。
然而,世界经济的发展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放慢了脚步(当然这不是由于《增长的极限》的警告,而是出于增长乏力的无奈),但逼近极限的速度却出乎作者原先的意料。在1992年版中,作者已明确指出,人类在许多方面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已经超越了极限,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这次的警告不再被当作危言耸听,因为当时的世界的确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危险征兆,例如粮食短缺、气候变暖、臭氧层被破坏等。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1992年召开了第一次全球环境与发展峰会,尽管会议没有取得什么真正有意义的成果,但从那以后,国际社会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忧患意识明显增强,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作为第3版,正如英文书名的副标题所表达的那样,本书是对第1版问世30年后所做的更新。从核心思想和主要结论来说,这一版和第2版一样,没有对第1版所表达的基本观点做出多少补充或发展,也没有做什么修改。那么出版本书的意义是什么呢?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的,第一,对数据进行了更新,大部分统计数据截止到2000年左右。第二,对模型技术也做了一些改进,新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更加精致并且便于运行。第三,使用了一些新的方法和研究成果,例如借用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发展出来的生态足迹概念,并且将其作为本书的一个核心工具。当然,第一点是本书最重要的“更新”之处,作者利用这些新数据向我们描述了当今世界的实际状态,并给我们提供了距离极限还有多远或者已经超出极限多远的直观认识。
也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本书还进一步阐明了作者一贯坚持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再次澄清了人们对《增长的极限》一书的一些误解。正如前面所说,我也曾对《增长的极限》一书的一些基本观点产生过误解,也听到过许多人对《增长的极限》一书的错误理解,所以我在这里愿意帮助作者再次澄清一下。
需要澄清的第一个误解是,《增长的极限》是不是对未来的预测?或者说,《增长的极限》是不是预言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崩溃”?乍看起来,作者所做的工作的确是关于预测的,他们使用了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基于当前和历史上的实际数据,对未来几十年的世界人口、经济增长、生活水平、资源消耗、环境等变量都做了“精确”的预测,为我们勾勒出了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并做出了“崩溃”的预言。但是,仔细阅读本书之后,你就会发现,作者并非进行单一的预测,并没有预言“崩溃”一定会发生,而是“模拟”了未来世界发展的各种可能“场景”。的确,在多个模拟场景中,如果人类社会照目前的模式发展下去,如果国际社会做出反应或采取行动过于迟缓,“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者也模拟了避免崩溃发生的情形,前提是国际社会及时采取行动、对增长加以约束并有足够快的技术进步速度。因此,《增长的极限》一书的主要工作是“模拟”人类社会的各种未来可能,而不是预测或预言地球和世界的某种必然结局。作者也多次强调,他们从模型中计算出的各种“精确”数据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这些数据反映出的发展趋势却是我们理解和展望未来发展必须关注的。
要澄清的第二个误解是,增长的极限是不是仅仅基于一些资源趋于枯竭的现实可能?这是批评者对极限是否存在质疑最多的地方,而那些相信技术力量将使极限不复存在的乐观派观点也正是基于这种误解。如果说极限的存在仅仅是由于某些资源会消耗殆尽的话,那么人们或许有理由相信技术的进步会为我们找到替代资源,甚至是发明不需要使用这些资源的技术。事实上,作者对增长的极限的关注绝不仅仅是出于资源枯竭这样一种可能,尽管这种可能性在今天看来已经非常明显并日益迫近。作者注意到了人口的几何增长,注意到了土壤肥力的下降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更注意到了自然环境所遭到的不可逆转的破坏,等等。即使某些破坏是可以逆转的,例如恢复土壤肥力,或者是通过技术可以弥补的,例如通过生物技术的进步来弥补土壤肥力下降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但是由于更多的资本将不得不转向满足维系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需求,工业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进而形成负反馈循环,导致人类经济增长趋于停滞。这是书中所模拟的崩溃发生的最主要路径。况且,还有些东西的破坏和失去是不可逆转的,例如臭氧层的破坏和全球变暖的趋势,至少目前看来不是技术的发展能够解决的,人类只能通过减少自己的生态足迹来避免进一步的恶化或放缓恶化的速度。技术绝非是万能的。
第三个误解是,作者是否在鼓吹“零增长”?零增长是人们对于《增长的极限》一书之结论和主张最简单的也是最普遍的解读,也是颇受人们诟病之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看来,这种主张无异于在扼杀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发展的努力,甚至被视为把发展中国家锁定在贫困状态的国际阴谋。事实上,作者的确提出要放慢经济增长的步伐以减缓向极限逼近的速度,但这种主张更主要的是针对那种增长高于一切、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的观点,也是对人类在贪婪地无限追求财富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这一现实的反思。在作者看来,如果能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如果能让全人类共享增长的成果,那么人类社会根本不需要这么高的增长就可以维持一种合意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本书所描述的所有场景中,作者模拟了各种可能性,如人口增长会保持在何种速度,如果资源的消耗速度能降低到多少,如果技术进步能达到什么水平……指出在这些可能的各种状态下,人类的经济增长会不会持续,能持续到什么时候。作者并没有提出零增长的主张,但在大多数场景中,模拟结果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如果人类不能对自己的贪婪欲望和增长的速度加以约束的话,最终的崩溃都是不可避免的;也只有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
本书的翻译工作最终由王智勇博士和我共同完成。王智勇翻译了第3~6章以及附录,我翻译了文前和第1、2、7、8章,最后由我统校。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我先后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充分利用这些地方良好的科研条件和丰富的研究资源从事自己研究领域的工作,翻译工作说是“挤”时间完成的一点也不为过。对于翻译上遇到的问题,特别一些关键词的翻译,例如“过冲”(overshoot)、“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等,我与王智勇博士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反复商讨,在意见不能达成一致的地方最后大多是按照我的想法敲定的。例如“overshoot”一词,本意就是“过度、过头、超过”的意思,但作为本书中的一个关键术语,必须找到一个词来突出体现它在这里的特殊涵义。我们绞尽脑汁考虑了各种译法,例如王智勇提出可以翻译为“超载界限”或简称为“越界”,但总觉得不尽如人意。最终我决定还是采用“过冲”这一物理学上的译法,以体现其作为一个术语的特殊性。所以,对于本书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或失误,我负有主要的责任。
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把本书的翻译工作交给我们,更感谢他们在本书的翻译由于我出国而拖延时所表现出的宽宏和耐心。感谢华章诸位编辑的辛勤工作,尽管我们从未谋面,但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对译者的尊重的确让我感动。
最后,我要借本书中文版的问世向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于2001年不幸辞世的德内拉·梅多斯女士致敬。她对世界与整个人类未来的深刻洞察和理性思考、对地球公民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怀和坚定信念,是我们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充满危机和挑战的时代最需要也最缺少的。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仰和学习。
李涛